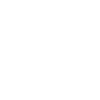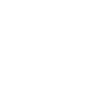我来陪你走一段
喜欢安安静静地看着他远远的走过来。

军人出身的他步伐端正大步,冷漠而英俊的面容自然流露隐约的威严。
三十五岁的男人,仕途一帆风顺,官已做到副厅级这个位置,当然有掩饰不住的骄傲吧?
他不。保持着一贯的正直豪迈,酒喝得痛快上来,管他上级下级,一律吵个脸红脖粗或是亲密得可以坦腹相对。
她常觉得他根本是大隐于市的出世者,在十丈尘世中自由的挥洒真性情,那份任性却也许是周围的情况纵容出来的。
“几十年是非曲直,功败自有人定。但一天不盖棺,一天不算数!”他在高官如云的公共场所笑嘻嘻的说。摆明了是自嘲,却借着酒意放肆地讽刺了一大帮人。就是在那个场合,她深深地为他不卑不亢、风趣洒脱的风范心折。
在他眼光不经意地和她对上的一瞬,她微笑,远远地朝他举杯。
他含笑,摇头,举杯,一饮而尽。
她笑得更灿烂了,调皮地冲他做了个OK的手势。
她确实不漂亮,但仰头旁若无人地笑的样子却真叫人不能抗拒,仿佛幸福也不过是如此。
他穿过喧哗的人群,来到她身边坐下。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今夜,她是拨动他心弦的那人。
酒逢知已,重逢恨晚。
她直言浏览他的疏狂与骄傲,却也不免劝他收敛一点。何必得失周围的情况呢?众人皆浊你独清是招人忌的。
这社会仍然是需要造假的社会。一定和否定只是群众的意见,上层有上层的游戏法则。
他重重地把酒杯一放:“总得需要一些人来说真话吧?得失——管他呢!”仰起头,又是一饮而尽。
她陪着他,从此也爱上微醺的滋味——灵魂脱离重重的的身体,飘在高处冷观,眩昏的人群,不明所以的高楼,一切没有道理却又不失秩序。
惟醉中知有天。
她突然之间晓畅他为什么爱饮酒了——微醺中的世界,一切不相关。
她是都市日报的记者。因一贯保持新闻的宗旨,说真话,不肯对某些人妥协,得罪了一些人而不好过。已经有人放风出来要整她。
她冷笑。是读书太多而中毒过深的缘故吗?她要在二十七岁的这一年,才惊觉她所了解所信赖的完全是书本上的东西。在真实残酷的人事竟争、排斥手段面前,她根本没有设防,自然也无还手之力。
是他心疼了她的天真,暗中出面为她将事儿摆平。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不逾原则的前提下,他乐意为她使用一些手上的权力。
她在好久后才懂得这件事,是他在背后的看护,让她顺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不言谢。因无言表寸心。只是在又一次相遇的公共场合上,她遥遥地向他举杯,不动声色地干完面前的一瓶长城干红。
那时候,已经闻言他正在低调地处理和妻子的干系。
有流言暗涌。无数轻视耻笑好奇猜疑的眼光,从四面八方投来,紧紧的将她笼罩。
她根本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一副“那又怎么样”的傲气,将所有自讨无趣的眼光逼了回去。
他更坦然。照常不躲不避,不慌不忙的约她一路散步。
冬天的傍晚,夜幕早早下降。十里长街,一盏盏亮起的霓虹灯在苍茫的暮色里分明迷离。
他最爱和她这样随意的在都市的街头漫步——多么象她对他的感情,是走到哪里是哪里吗?
是真正的暖昧。
旁观者都以为他们的干系从俗,却极少人懂得,他们之间其实没有实质的内容。仿佛隔了一道透明的玻璃,看得见彼此,却走不已往。
他和她的干系纯粹属于精神层次中最详尽的创建,没有渗透进一点生活的粗糙面。
她知道他所处的情况已经够阴郁够重重的,所以不肯再给他添任何不快。她努力让他们在一路的每一时光都过得精致而生动。至少,她要他记得的,都是她的笑。
有了饮酒的心情,他一个电话过来:“晚来天欲雪,”
她很快答应:“可饮一杯无?”
呵呵。他大笑。
醉乡有路宜频到,此外不堪行!她依然幽默。
他酒至一半,突然之间正色,唤她的小名:“小宝啊小宝,如果我现在依然二十五岁,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她故作失色,笑吟吟地道:“啊——你以为,我现在又肯放过你了吗?”
他一本正经地追问:“那么,你想怎么样?”
她飞了个媚眼:“你说呢?”声音又娇又嗲,让他差点不能自持。
他一口酒下去,大声嚷嚷:“啊,小姐,你在诱惑一位绅士做不品德思想。罚一杯。”
她更笑得象个孩子一般,无赖得让他心软。
十二月,他往北京开会,天天贴身穿着她赶织给他的银灰色羊毛 衣。
返来的那天,京城的天空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
他打开手机让她听下雪的声音。
她笑,如孩童般柔软的请求:“给我带一个雪人返来吧。”
他无视同行笑话的眼光,在机场的雪地上蹲下,挖了满满一掌皎白的雪,装进一个玻璃瓶子里。
她在机场接他,看见他远远的向她扬起手上的玻璃瓶,欢呼起来。
雪在暖气室里一点一点的融化,他摇晃着半瓶子的雪水逗她道:“雪人都是水做出来的,哪象你——冰雕的”
她白他一眼,高高兴兴的将这半瓶子雪水存在冰箱里,很快冷冻成一格四四方方的冰。
深夜,他会突然之间之间之间打来电话,责备:“还不睡?”
听见得背景流动着细细碎碎的音乐,他知道她又在听他送给她的那张《悲情城市》。
她故意赌气说:“要你管!”
她是一个不太珍惜自己的人,生活散漫而自由。
他不是一个爱管人的人,却也管了她好几次。
他知道她一贯失眠,有熬夜的习惯。他熟悉她过后,便再不许她吃安眠药,担忧她养成对药物的依赖性,也不许她再通宵达旦的上网、写稿。
她微笑:“怎么,官越做越大了吗?管你那个部门不够,还想越界呀?”
他老鹰(eagle)抓小鸡(chick)般把她拎起来,凶巴巴的道:“谁叫你在我的统领范围之内!”
久不晤面,他看见她的第一句话便是疼惜:" 咦,又瘦了嘛?" 从今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那又是为什么呢?
她笑笑。
他每日的饭局排得密密的,却也不见他胖。
他常抓着她陪他出席,不许别人哄她饮酒,却逼着她喝完满满一大碗的汤。
他牵着她的手过马路。
他的手掌大而丰厚,干而温暖。暖意从他强有力的心脏流到他的手,然后传到她冰冰的手指,慢慢到达她的心窝。她乖乖地让他紧握着她纤细的小手,多么希望前面永远是绿灯呀。
却在中途,绿灯突然之间之间之间转为红灯,他们被迫停在街中心的安全岛上。车流汹涌,咆哮着穿梭过,险些要将他们沉没。她不禁向他身边挨近,再挨近。
他对她笑笑。
这一刻,她确信他是她唯一的依靠。在他的眼中,她看得见自已。
也许,他不会是她的开始,也不是她的结束;也许,可以说是不经心,也可以说是透彻。但,凡事都必须要有个形式的吗?他们都不是善于为自己的生活一丝不苟的人,总是要旁边看着的人来替他们生气。可又有什么盘算的呢?感情这东西,没有什么好抱怨,都没有什么好矫饰。事儿最严重——也不过是一笑。
她在做出决定前,什么都没说,独自离开,出外面走了一圈。
她在海边的一个小镇上住下。
白天,她只套件宽松的褐色毛衣,一条泛白的牛仔裤,把手插在裤袋上,悠闲地走遍小镇的每一角落。
傍晚,她一脚高一脚低的踩在柔软的沙滩上,看火红的夕阳挂在远远,蓝蓝,灰灰的海那边,看海面上归帆片片,渔灯点点。
她有时会呆呆的看着那些正在赶海的勤劳朴素的老人,孩子,女人出神。
她特别羡慕那些张着大嗓门,亲昵地数落丈夫吼骂淘气的小孩,手脚麻利勤快善良的村妇们。每一个女人圆圆的脸庞上都洋溢着简朴 ,满足的笑脸,够康健够强壮。
小镇生活的这几天,她以为可以完全的扔掉另一世界的思想和思 念。
甚至以为,就留在当地不走了吧,嫁一个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和你谈诗书论人生,却懂得殷勤照顾你的温饱,一个康健粗犷的打渔郎,一群活蹦乱跳的小孩,就那样吵吵闹闹的过一辈子也是种幸福吧?
寻常人家自有寻常的幸福快乐。
第一次,她觉得她读过那么多的书与所谓的幸福根本无关。善于思想,也许只是比一般的人更善于寻找烦恼。
她回到省城,回到家,打开电话答录机一条条的听留言信息。
前面都是几个不相关人的寒喧问候,前面——竟全是他自言自语的心情。
他明知道没有人,也许他就是不要人听,对着沉默的发话器嬉笑怒骂——“小宝,你不乖,偷偷的跑哪去了?”
“你以为你真是第二个三毛啊?撒哈拉沙漠都没有第二个荷西在等你了!”
“小宝,你不在,寥寂无人省呀”
“我在认真的考虑我们的干系——”
她抱着答录机坐在地毯上,一句一句的听他的声音,泪水一点一点的滴落下来,敲痛了心。
她努力着,用心的不去想那几个字——拣尽寒枝不肯栖。
如果,如果那只是他酒醉时候的说话,算数吗?她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在清醒理智的思考他们之间的干系。
他找到她,将她紧紧的抱在贴心的胸口上,叹气说:“别以为我是和你玩假的。”
她仰起脸,仔细的看他的眼睛,嘴角含着冷与倔强的笑:“我要求过什么吗?!”
是的,也许就因为她对他从不要求,也从不埋怨,才更让他歉疚 吧?
他一向以为他在政界上的玲珑是一场大的游戏,在感情生活中也是主导者,进退攻守间,一切自有分数。
遇上她,才发觉另有比他更高明的人。只因为她根本不要做他的对手,完全消极的将自己抛现在最前线上,不进攻,也不抵抗。他以为走进了一个空城,其实却是一个迷城。
她和他的前妻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个女人。他的前妻是一个过于活络的女人,外比武段是一流的,做任何事儿都有目的有打算,哪怕是不择手段也要完成。二年前凭干系调到京城后,他们之间的夫妻生活已是名存实亡。但前妻一向抓着书记夫人的头衔不放,直到出了国,结识更好的人,才迅速赞成离婚。
他想,其实男人们要的幸福都很简朴吗?一个聪慧可人的妻,一个活泼生动的小孩,一份足以自傲的事业,平平安安的活下去,老下去。
她会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把火焰吗/ 她带给他前所末有的热情、快乐和舒适,却也让他心惊——这个女孩儿太聪慧了。
他恐怕她是根本不属于任何人的。
这次,她不声不响的独自出外面走一圈返来,整个人更加沉静,更加内敛。象一只安静地躺在海底的珍珠贝,在阴郁中抖擞温柔的光芒。
他也曾试探她:“早点嫁人吧,别耽误了自己。" 她眼皮也不抬:" 再说。" 口气淡淡的,竟是翻版了他习惯应付别人的官腔。
他有时颇为困惑:" 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了解你。" 她干脆背转身:" 我从不知道你原来也有这么旺盛的好奇心。" 然而,不谈已往是不可能的。已往也是造成昔日生活方式,个人性情的一部分。
他的背景虽然显赫,感情生活却异常简朴。他与前妻是直接从初恋迈进婚姻里面的。外头形形式式想接触他的女子不少,他却不为所动。他想,他这一辈子,仅应付两个女人已经够累了。
她却从不肯多说她的已往。
二十七岁的单身女子,没有过一些故事是不可能的 .他很想知道,是什么让她在感情的路上踟蹰,在婚姻的门前踌蹭迟疑?是谁在她的腕上留下一道浅浅的伤疤?
她只在一次酒后落过泪:" 新鲜,以前倒是真的爱过他。" 是哪种感情使人如此沉默,甚至绝口不提呢?
她不说,他不再问。
他最写意的是,他们之间一向没有陌生感,都没有距离感。也许因为空白太大,反倒有更多的可塑度。
他畏惧的是,在这一年龄才要开始一件事,伤害已是必然。
端为不使这件事变成一分希望,他没有自动进行。
她眼中深深的寥寂,看了简直要教他愤怒。她到底要些什么?他。又能给她什么?
静下来时,他先会觉得自己的心态很可耻,之后是可怜。年龄不小而爱情用得太少产生的迟惑。
他醉了,躺在长沙发上,一声声的唤她:" 小宝,小宝" 她在心底应:" 我在,我在。" 她用白毛巾绞了热水,给他洗脸。仔细的抹过他饱满的额,浓黑的眉,高挺的鼻,方方正正的下巴。
三十五岁的男人,闭上眼睛,睡着了也就象个小孩。紧蹙着的眉 头,锁着一点点不快乐的神气。
她忍不住用修长的手指轻轻的去抚平他额头上锁起来的皱纹。
半夜醒来,有个人可以依靠,可以倾谈,而他确实是你的,那是一份完美吗?
她不知道,该是谁来补她生命圆圈中缺的那一角呢?
是他吗?
然而谁又可以和谁承诺一生一世,谁又可以和谁缠绵终老?
终究都是要离开的。
她叹息,俯下身子,温柔地亲他的眼睛,低低地在他的耳边喃喃细语:" 我来陪你走一段。"
上一篇《“郎财女貌”?——简论为何富翁的太太多半儿不是美女》故事精选
有篇文章提到,在纽约曼哈顿,至少坐拥一千万美金才算中产阶级。或许你不信,那就看看曼哈顿的房价吧,哪怕是穷人住的最便宜的合作公寓(Co-op),都得五、六十万 ..
文/新浪网友 冰雪儿 图/赵婷 认识洪的时候我的感情世界一片空白。 认识洪的地方是我们这个小县城唯一的大众舞厅。 认识洪的时候我的身份是分居,而他是 ..
猜你爱看
- 1 “郎财女貌”?——简论为何富翁的太太多半儿不是美女
- 2 坐台女友你到底为爱还是为钱
- 3 在爱与性的边缘
- 4 口述:我不后悔为网恋失去处女身
- 5 结婚20年我发现丈夫有私情
- 6 蓝色手机的爱情故事
- 7 网来的美人鱼
- 8 年轮日记:一曲无爱的情歌
- 9 嫁给肯背你上楼的男人
- 10 拂晓时分
-

希腊神话30篇完整版
1、尼俄柏希腊神话2、乞丐奥德修斯来到大厅希腊神话3、俄狄甫斯和波吕 ..点击量: 3800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热门15篇
1、彭忒西勒亚希腊神话2、天马与王子希腊神话3、赫拉克勒斯为翁法勒服 ..点击量: 2308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600字锦集
1、美狄亚和埃厄忒斯希腊神话2、赫拉克勒斯和阿德墨托斯希腊神话3、围 ..点击量: 1416 | 时间: 2025-06-02 -

爱情故事100个
1、静候一次回眸爱情故事2、就是这个温度爱情故事3、单车上的爱情爱情 ..点击量: 2602 | 时间: 2025-06-02 -

中国历史故事全文九个
1、中国历史故事:盘点中国历史上那些经典阅兵中国历史故事2、军法始于 ..点击量: 2016 | 时间: 2025-06-02 -

格林童话十个内容
1、金钥匙格林童话2、金鸟格林童话3、蓝灯格林童话4、狼和七只小山羊格 ..点击量: 3312 | 时间: 2025-06-02 -

安徒生童话短篇五个
1、天鹅的窠安徒生童话2、梦神安徒生童话3、飞箱安徒生童话4、大门钥匙 ..点击量: 2814 | 时间: 2025-06-02 -

益智故事完整版1300字
1、顺势趴下并不是屈服的智慧益智故事2、龟兔赛跑益智故事3、认同自己 ..点击量: 1564 | 时间: 2025-06-02 -

罗马神话五个免费
1、狄安娜和阿克泰翁罗马神话2、俄狄浦斯的故事罗马神话3、庇格玛利翁 ..点击量: 1546 | 时间: 2025-06-02 -

历代名女名妓七篇推荐
1、谢道韫临事不乱历代名女名妓2、中国历史上十大名妓之死——玉堂春尽 ..点击量: 1889 | 时间: 2025-06-01
本站名称: 狸猫故事(m.limaogushi.com)
内容收集于网络或由网友投稿提供。
如有侵权请迅速联系本站,本站在核实后立刻作出处理!
Copyright ©狸猫故事 2019-2022 故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