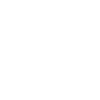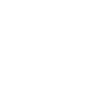幸福是天上的云

幸福是天空上的云
一
窗外是一株枝繁叶茂的石榴树。娇柔的石榴花开了满树的鲜红,艳艳的,娇羞羞的红。程彩衣一向认为,虽说石榴花开的很热闹,很鲜艳;可那花的片儿太薄了,拿一片迎着阳光,透过阳光,那只是淡薄薄的一片红,看似一个苦命相,就连那详尽的花托儿都瘦伶伶的,甚是可怜。程彩衣觉得明天自个儿就是一朵石榴花,怯生生的开着,热闹闹的透着一种可怜的单薄。是的,程彩衣此时也是一身的红,坐在铺着红床单的床上,倚在折叠整齐印着小胖孩抱鲤鱼(carp)的红缎子被上。是的,明天是程彩衣大婚的日子。新娘子程彩衣坐了车从县城嫁到几十里外的这个刘家庄。喇叭一任儿的热闹着,也有热闹着的人们。拜了堂,送进这间房,都几个小时了,就没一个人出去闹洞房,这在皖西北是不寻常的。
是的,是因为新娘子。程彩衣苦笑了一下。是的,是因为她。程彩衣怔怔的看着墙上挂的结婚照。大大的眼,白净净的脸,她就那样挂在墙上低眉顺眼,一脸的落寞与迷惘。她的旁边是一个年轻的男人,浓眉呆眼,很平常的,有点呆相的一个男人。这就是她的男人,这个刘家大院里的大儿子。他下面另有老虎(tiger)样的五个没结婚的弟弟。两个没成年的妹妹。这个家除了人就只有穷了。是的,是谁这时候都能看出来了。程彩衣有毛病。程彩衣一定有毛病。这样的家一般农村妹子都不愿嫁的。别说城里人了,更不要说依然个颇有几分资色的城里女人了。是的,程彩衣有毛病。有一眼看得出来的毛病,她的左腿有点瘸,在刘家庄人的眼里她是个瘸子。可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主要的是她另有人家看不出来的毛病。是的,精神病。程彩衣另有精神病,也就是农村人常说的神经病。这刘家人并不知道,这刘家庄的人就更不可知了。这也就是县城的高中生颇有几分资色的程家唯一的女孩儿子程彩衣嫁给刘家庄最熊又最穷的刘老呆的大儿子的一切因由。
程家人都觉得这是彩衣的福。彩衣也这么觉得。她从十七岁说亲到现在二十五岁,八年里见过无数男人。不是瘸就是傻,正常点的又都是四十岁以上的老王老五骗子。那天刘家老大一进她家的门,她就看见上帝对她笑了。他不俊,面相另有点呆。可他不瘸也不傻。他还年轻。和她一年生的人,都是属羊的。依然同一个月份生的人,都是石榴花盛开的五月。这就是了,就是他了,他是老天爷派来的,为她程彩衣派来的,她知道。
他果然是老天爷派来的,婚事顺利极了。现在,彩衣坐在铺着大红床单的床上,真的有了一点新嫁娘的心情,一丝丝的喜,一点点的羞,又有着一缕淡淡的愁。是的,她怎么能不愁呢?她不光有点愁,她另有点慌。她又怎么能不担忧呢?相亲的时候她吃了药,他看到的她只是一个腿有点不方便的长的悦目的大龄姑娘。是的,家里人隐瞒了她的病,万一他知道了,那他?彩衣不敢想。她按了按她衣袋里装的药。她等着,她要在他进屋的前一刻吃下去,八个小时,她只有八个小时、、、、、、
那一晚没有发生让彩衣担忧的事。丈夫是个实心眼的人。见了花儿一样的女人自己先软了。一心儿里都是满满的疼。面呆的男人心却细,轻手轻脚的极尽温柔体贴、、、、、、屋里红烛摇曳,屋外星星眨着眼睛,石榴花儿静静的开、、、、、、
彩衣醒来,窗外淡淡的晨曦静静的映入室内,丈夫还没有醒。她摸索着从衣袋里抠出三粒药,干咽下去。平静的躺在床上,嘴里有一丝涩涩的苦味,心里却有一抹甜。彩衣静静的躺着,她听见外面的鸡的叫声,狗的叫声,一
切都热闹极了,一切都幸福极了。是的,是幸福极了。彩衣觉得就这样,她就这样一向躺下去,躺在这一片淡薄的晨曦里,躺在这一片鸡啼狗叫里,躺在这幸福里,一向躺下去,一向躺下去、、、、、、丈夫醒了,彩衣沉着闭上眼。丈夫穿衣服,丈夫下床,丈夫出去了。彩衣羞怯的听着这所有。等那门轻轻的一响,彩衣就一下坐起来,把羞红的脸埋进了被子里。丈夫再出去时,彩衣已经穿好啦衣服坐在了大床边上。丈夫是端了盆洗脸水出去的。彩衣洗脸的时候,丈夫铺床叠被。彩衣洗好啦,彩衣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发。丈夫没有去泼洗脸水,丈夫一向走到她身后,丈夫轻轻抱住彩衣,丈夫把脸慢慢埋在彩衣的长发里低低的说了一句话,“我会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是多久?彩衣不敢想。如果他知道了自己是个,如果他知道了她这样瞒了他,如果他知道她只是一个只能靠药物来在世的人,如果他、、、、、、 不管彩衣怎么想,那天过得还不错,一切都顺利极了。吃过早饭,收拾了回娘家。一向到彩衣又坐在程家那张她躺了八年的床上,她都没有出错。一切正常极了,一切好极了。 奶奶和嫂嫂都很高兴,爸和弟也很高兴,程家一家人都忙着招呼回门子的新女婿。所有的人都快乐着。所有的人都忙在世。只有彩衣闲着,一个人坐在她以前小卧室里的床上。彩衣又被程家人习惯性的疏忽了,就象这之前的八年一样被疏忽了。 二 彩衣狭小的内室里,除了一张床,就是一张桌子,别的再都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如果要说,那便是她床前是一扇朝南的窗。窗外院子里是一棵石榴树。这是一棵她看了八年的树。这棵石榴树比婆家的那棵老多了。这棵树一年开多少花,发几枝杈,她都知道。有多少朵花变成为果,有多少朵花在在雨中凋谢,化成泥在岁月里永远的沉寂。她都知道。在程家,没有谁比她更知道这棵树了。八年来她每日的分公秒秒都是看着这棵树熬过来的啊。 这棵树刚种下时候的情景,彩衣记得最清楚。那天是个傍晚,平建把这棵树送给她,她拿返来偷偷种到院里她内室的窗前。提水的时候被妈妈看见了,还问她。她红了脸什么都说不出来。妈还开玩笑说:“这丫头,大了,晓事了。明儿,我得找平建的妈说说,我可不能白给她养个闺女。这小时候的事可不能算。”彩衣妈宁静建妈是一个厂的好姐妹,两个人好的给一个人似的还不算,又给儿女定了娃娃亲。从彩衣记事起,平建妈就没少说过这句话,“嗨,可不敢把俺乖媳妇给累着。”平建也识趣。虽说两个人同校不同班。可每日下了晚自习,他总站在学校门外大槐树下等彩衣。两个人虽然不多话,可一个前,一个后的就这样走了许多年。那是彩衣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日子。 可这日子在妈妈走了以后就没了。彩衣清楚的记得,那一天天好热。妈妈下班返来,收拾好啦饭菜,人都上桌了,妈妈又想到忘了主要的东西在厂里。妈妈叮嘱一家人先吃,她推起车子就要走。彩衣刚好要买一本很主要的学习资料,就顺便叫妈妈带她去。娘儿俩骑车快快乐乐的出门。可是再也没能快快乐乐的返来。一场飞来的车祸,妈妈走了,彩衣也躺在了医院里。一个月后,彩衣出院回到家。家里没有了妈妈,妈妈永远睡在了山上,彩衣也成为一个瘸子。彩衣怕,彩衣不敢出门,彩衣不能想象别人眼里的自己,彩衣、、、、、、彩衣真的不想活了。平建再也不来了。彩衣不再出她的小屋,她觉得只有小屋才是安全的,小屋就象妈妈,躺在小屋里就象躺在妈妈的怀里。就这样躺着吧,永远躺着。她不再和任何人说话,她天天呆呆的看着窗外的高高远远的天空,看天空上的云,看那云在慢慢的转变,一会儿看出平建,一会儿看出妈妈。一天,她突然之间尖叫起来,扯破了喉咙的叫,一向叫,一向叫、、、、、、全家人都来了,谁也不能阻止她。她疯了,彩衣疯了,人都说彩衣疯了,彩衣 真的疯了。 有一段时间,彩衣总觉得自己永远活在了十六岁。平建,妈妈,同学,老师,数学题、、、、、、 彩衣醒过来时,她已经十八岁了。窗外的石榴树有杯口那么粗了。大哥娶了大嫂也已经分出去住了。二弟下学出去打工了,小弟也上高一了。愁苦的父亲(father)整日不在家,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天天在家照看着这个家,照看着她。 是的,她瘸了,她疯了。每日奶奶都拿着三粒血红的药丸叫她吃。她知道她是疯了,只有有了它她才真正的在世。 她在世,她每日就这样坐在这间小屋的床上望着窗外在世。 春天,石榴树绽开了嫩叶;炎天,石榴树绽开了花朵儿,红红的,薄薄的,在热闹里反又显出几分落寞来;秋天,石榴树挂果了,压的枝条垂下去;冬天,白莹莹的雪粒子挂了满树的银闪闪。 花开花谢,一年又一年,她也象冬眠的蛇(snake),有时蓬蓬勃勃的开着;有时又死寂寂的;一半清醒,一半迷茫。平建上大学去了,平建工作了,平建娶了媳妇了,平建把他娘接走了,这个小区里就这样没了平建 的影子,就好象从来都没有过这个人似的。 二十五岁了,彩衣看着窗外的那棵石榴树,石榴树也有小碗口那么粗了。老了,石榴树也老了,老了条子也就糙了,花也就稀了,挂的果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老了,真的是老了,石榴树真的是老了。男人彩衣是见了不少了。也是一个不如一个了。最体面的是那个小伙子。他什么都好,就可惜是个哑巴。最差劲的是那个老头子,一身肮脏,满头白发,比彩衣的爷爷面相还显老。但人还精神,一见彩衣就两眼冒光。气的奶奶直哆嗦,手指着媒人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彩衣知道奶奶也是没有办法,彩衣知道她已经成为了这个家的绊脚石。两个弟弟都到了要说亲的时节了。可是家里有个没出嫁的疯姐姐,就象一块破补丁让他们抬不起头来。尤其小弟的那个女朋友都谈了两年了就是不说结婚的事。彩衣知道她该走了。可奶奶看的紧。她一向没有找到符合的机会。她想好啦,她开始攒安眠药。她打算攒一百片,吃了就救不返来。就在她攒到八十八片的时候,她等来了他。她的男人,刘家老大。男人是寻常的,不起眼的出力干活的乡下男人。可却是她见过的最好的一个。爷奶哥嫂都很写意,对年轻人出奇的热情。小弟一口一个哥的叫,叫的比亲哥都亲。家里瞒了她的病。只说她出了车祸,腿落下了毛病。幸亏男人家离县城有六七十里地,在这县城人生地不熟的,只说在城里找个零活干,没想到招了这个亲,男人显而易见很快活。彩衣想说什么,被嫂嫂狠狠在腿上掐了一把,她的手脚也就软了。再说彩衣想自己也是个女人,总也不能白来这世上走这一趟,怎么说也要当一回新娘子吧。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能给家里去了她这个负担,也算她对爹娘报这养育之恩了。只是可惜了这小伙子。可谁让他这会子就撞上来了呢?想来这也是上辈子注定的吧。 老天真的待她不薄啊!彩衣想着往事,看着外屋和家人说话的男人,她的心里充满了柔情。哥,彩衣在心里叫着,哥,这辈子彩衣欠你的,下辈子再托生彩衣还做你的妻,伺候你一辈子,爱你一辈子。 杂乱而长久的回门在彩衣一家的热情招待里很快就已往了。一对新人也要回去了。临走时,奶奶抓着男人的手,一个劲的叮嘱,嫂嫂暗地里又偷拧了彩衣几下子,叫彩衣多长几个心眼。 家逐步的在视线里远去了,最终只剩下奶奶的一个孤独而又模糊的影子。彩衣知道她已经不再是这家里的人了。娘家人伺候烦了她,也打心眼里看不上男人。这不是嫁,这是娘家人在把她使劲往外推呢。彩衣知道她什么都没有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另有的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了。他将是她一辈子的依靠。坐在男人的车后座上,她轻轻把脸伏在男人并不开阔的背上,在心里叫一声,“哥,你可不要不管我,我只有你了,哥?” 男人转头对彩衣一笑。彩衣忍不住就掉下泪来。男人转头用粗糙的手给她轻轻擦掉,“傻样儿,哭啥?啥时候想家了,我就带你返来。”男人以为彩衣是舍不得离开家。 三 婆婆一家对她都好的不得了。怕她是城里人,吃不惯乡下饭菜,就在小锅里单给她炒菜;怕她在屋里呆着闷,妹妹常扶了她出来,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妹妹还邀了村上的小姐妹,叽叽喳喳围着她说话。公公给她做了条拐棍;男人出去干活,多会回了家,脸都不顾得洗,就先到屋里看她一眼,多会怀里不是摸出个枣来,就是摸出个杏,塞到她嘴里,看着她吃,自己眯着个眼笑。彩衣觉得她是幸福的,这会儿就是死了也没白来这世上一趟。 可彩衣也是恐慌的。她夜夜醒来,偷偷捏着衣袋,药是吃一粒少一粒了,眼看就要没了。临来时,嫂嫂说过一段时间让小弟给送来,让彩衣不要给男人说。反正彩衣一个月有二百多块钱的低保补助,用来买药还能顶得住,月月按时让小弟送来,能瞒一会是一会。彩衣知道娘家人是指望不上的。事是早晚要说的,人人都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可是彩衣也依恋眼下这日子。她不敢想象婆家人知道了真相会怎么样想,也许去娘家闹事,也许会赶她走,也许是、、、、、、她是该死的人,眼下这幸福是梭子里的布能织多长是多长,可药不等人。明天再吃三粒,就另有九粒了,三天的清醒,三天的幸福、、、、、、 彩衣手哆嗦着把药塞进嘴里,她越过睡着的男人,去端桌子上的水杯。不提防男人一翻身,啪,水杯掉在地上碎了。男人惊醒了,看见灯光下满脸惊恐的彩衣和彩衣紧闭的嘴。“你,你咋得了,谁欺负你了?你,说,你吃了啥了?你?、、、、、”男人下意识的去拍彩衣的脸。彩衣嘴里的药片印进男人眼里,男人惊慌的去抠彩衣嘴里的药片,抠出来,扔出去,还一个劲的问,“咋了,你咋了?谁,是谁?你说啊?”粗笨的男人还以为是彩衣有什么想不开,寻了短见。 唔、、、、、、彩衣伏在被子上大哭,哭泣了一阵子。彩衣喝了水,捧住水杯向男人讲起了真相。从平建,到妈,到、、、、、、八年来的事彩衣都讲了。彩衣还把衣袋里的药瓶子拿出来给男人看。彩衣哭好啦,讲完了,彩衣就等着男人发火,打人、、、、、、 可男人没有,男人很平静,男人打开药瓶,取了三粒药,放到彩衣嘴里,又拿了水给彩衣喝下去。放下水杯,男人用粗糙的指肚抹干彩衣嘴边的水迹,抱住彩衣说:“俺是个粗人,只上太小学三年级,没文化。俺不懂什么大道理,俺就知道不管咋说,是俺娶了你,俺自己找的,也没人害俺,也没人逼俺。俺娶了你,你就是俺媳妇。这一辈子,俺就得养着你。” “哥。”彩衣把脸埋在男人怀里泪水滔滔,“哥,这一辈子彩衣欠你的,下辈子托生彩衣还嫁给你,好好饲待你。哥,哥、、、、、、” 彩衣是幸福的,毫无疑问,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彩衣胖了,眉眼上尽是笑,连她看着那棵石榴树的眼光都是柔和的。婆家人知道了那件事。可婆婆和她说话依然那样软声软语的;妹妹依然常给她梳各样的辫子;婆家小弟也常来请教数学题。彩衣是幸福的,桌子上搁着几瓶药,是男人去县城买的。彩衣看着这个家,巴不得把这个家捂在她的心口上,彩衣最想做的就是给男人怀个孩子。 四 看婆婆的意思,这根本就不算个啥。婆婆一辈子生养了十几个孩子,养大的有八个。这家人看惯了女人生孩子,认为这是不值得说的事。男人在这个事上也没啥念头。可彩衣想,彩衣一边想早点怀上个孩子,稳固自己的家。彩衣想男人在外面干活,回家有女人,有孩子,这个家才欢实,才更有奔头。彩衣才会觉得自己也和别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彩衣才觉得托生个女人来这世上走一趟也算活齐全了。可彩衣也怕,怀了孩子,彩衣就不能吃那个药了。不吃药,彩衣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样子。可彩衣得跟自己赌一把。男人现在不上心,一年、两年后依然会想到孩子的。彩衣不能等到自己被人嫌。就是死了,只要能给男人留个全乎的后,彩衣觉得也算对得起男人对她的疼。 彩衣的肚子果然争气。进门三个月后,秋霜来了的时候,她怀了孩子。婆婆甚是喜欢。只是男人少了晚间的那一口,多少有点没趣,可对彩衣越发的好啦。那个药是不能再吃了。彩衣日夜睁着两只眼,她不敢合上,怕合上了再也不会醒来。她什么时候会?人家都说疯,彩衣不说那个字,她只说梦。是的,怎么是疯呢?她就是做了一个梦而已。彩衣怕做那个梦。彩衣不知道那个梦里会不会有男人。“哥”,彩衣在心里喊,“哥,帮我,哥、、、、、、”彩衣怕做了那个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醒来。象她第一次做那个梦,睡着的时候她记得她才十六岁,她在梦里笑啊,跳啊,永远的十六岁。可是她醒来的时候却是十八岁了。彩衣不知道这一次她会做多久。彩衣怕,彩衣不要做梦。“哥”,彩衣在心里喊,“哥,抱着我,我怕,哥、、、、、、” 彩衣看着自己的肚子。婆婆说有四个月了。可她看它还那么平坦,怎么会有一个小孩子躲在里面呢?她出神的看着自己的肚子,她看见肚子象个门一样的打开了,一个穿红肚兜的小女孩儿走了出来,嘴里叫着妈妈,向她跑过来。她伸手一抱,原来是自己趴在妈妈的怀里。妈妈训她不听话,妈妈就打她。她爬起来就跑。前面有条河,平建在河那边笑,叫:“彩衣,你过来啊。”彩衣跳到河里,水彻骨的冷,彻骨的痛,彩衣听到了自己的叫声,象个受伤的野兽、、、、、、 西天有朵云,慢慢飘散,云散作了千万缕,片片皎白轻盈,柔柔的浮在湛蓝澄明的天空上、、、、、、 彩衣慢慢睁开眼睛,看到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结婚照,女的是她;男的,她怔怔的看了看,慢慢的一滴泪滑下来,“哥!”她在心里痛楚的喊,“哥!” 是的,梦醒了,天晴了。家依然那个家,男人依然那个男人。不同的是彩衣的被窝里多了一个小家伙,一个三个多月的小女孩儿儿躺在包裹里,两只眼睛睁的大大的,圆圆的、晶晶亮的望着人。这就是彩衣的闺女(daughter)小雪。彩衣从婆婆埋怨的语气里知道了小雪是个先天残疾儿,脊椎弯曲,内脏移位。天啊!闺女,我的闺女啊!我的小小的闺女啊!彩衣的心碎了。她可怜的闺女啊,难道她这一生、、、、、、彩衣实在难以想象她幼小的闺女终生弯腰弓背的生活在人们诧异的眼光里。天啊!我的闺女,我可怜的闺女,我的小小的闺女啊! 婆婆念叨着,说我们老刘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啊!娶了疯媳妇不说,还生了个怪孩子。只有男人,男人什么也不说。可彩衣从男人青筋暴跳的额头上看到了男人难隐的屈辱和伤痛。彩衣知道在乡下男人娶个问题媳妇多半人还能接受。不为女人还不为个传宗接代吗?齐整的女人在乡个生不出孩子也是没人待见的。现在她、、、、、、彩衣知道男人在外面一定是受了委屈了。“哥,对不起。哥!”彩衣在心里痛喊着,彩衣知道,她和她的闺女在村里已经成为老刘家的一块伤疤。天啊!老天啊!彩衣无力的倒在床上。她甚至没有勇气去抱她的闺女。婆婆虽然嘴里念叨着,可终归依然个善良的乡下女人。她抱孩子,喂奶,换洗尿布。小雪不象是婆婆的孙女,倒象婆婆自个儿生的孩子。婆婆也是个可怜人。她一辈子也没出过孩子窝。 小雪百天了,小雪会笑了,小雪、、、、、、婆婆抱着小雪逗给彩衣看。彩衣汪着两眼泪,心象针扎一样痛,把小雪紧紧抱在怀里,“老天爷,有啥罪都让我来受吧。可怜可怜我的孩子吧!保佑她平平安安的,保佑她长大了找到属于她的幸福吧。” 老天爷没有听到彩衣的祈祷。小雪病了。夜间起的热,来势汹汹。临天明,公公和男人就送婆婆和小雪去了县医院。彩衣在西屋里呆呆的坐着,她已经不再向上天祈祷 了,上天也不保佑她的小雪。她都不知道还该向谁祈祷。她听到小雪八十多岁的祖奶奶在堂屋里念经的声音。她不知道西天的佛会不会保佑她的小雪。 下午公公返来了,脸阴着,只说小雪先天性内脏移位,医生说先住着看。临傍晚男人返来了。彩衣不敢问。男人也没提小雪。男人只说了一个笑话。说婆婆在楼上都迷向了,叫她下楼买包子,她转了几圈都没找着门上来。护士把她领上来,她居然说这医院的楼门都一样,看哪都一样,摸了半天依然个错。依然城里人历害。男人说完嘴角咧一下,象个笑样,可比哭还难看。彩衣也想给男人一个笑,嘴一咧,没笑出来,泪却滚了下来。 老奶奶念的经毕竟没有救回小雪的命。半个月后,婆婆也返来了。彩衣看着婆婆身后的眼光织成为一张网,织得那么稠,那么密。男人看彩衣的那个样子,心疼了,男人抱住彩衣,“咱以后再要一个。”彩衣的心碎了。她的小雪完了。她的小雪连个坟都没有。彩衣知道乡下人隐讳这个,没成人的孩子不能修坟,就是成为人没成家的年轻人死了,家里另有老人在那也是不能停尸在家的,只能在村外搭个棚草草埋了了事。死了也是决不能进祖坟的。小雪有祖奶奶,奶奶,爹娘,况且她依然个未满周岁的孩子。乡下人认为这都是没成人的,还只是个魂,是来报应爹娘的。没有埋的,只有丢河边野地里让猪拉狗嚼去。这样她就不会再来报应人了。只能成为孤魂野鬼,受尽凄惨。小雪,我的孩子啊!彩衣在心里悲嚎着,小雪,你走慢点,娘来了,娘要护着你、、、、、、 彩衣看到小雪笑了,小雪长大了,小雪在前面跑,笑的咯咯的。她在前面追。娘俩跑着跑着,倒在草地上,滚作一团。彩衣听见有人叫她。转头一看,看见娘站在草地上手里拿着个饭盒叫彩衣吃饭。彩衣偎在娘的怀里,小雪躺在她的腿上。彩衣看见天空上太阳出的很明亮,一朵朵艳白色的云飘浮在金黄色的天空上、、、、、、 逐步的,白色的云浓了、浓了、成为黑漆漆的乌云,沉沉的压在天空上,嚓,一道闪电撕破沉闷,哗、、、、、、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五 彩衣看到男人在雨中使劲的拉一棵树,男人消瘦的身体使劲的拉那棵树,男人跑进屋,一脸的雨水。男人看到彩衣明静的眼光,男人笑了一下,走过来坐在床边:“你醒了。”男人不说好,说醒。彩衣知道自己又一次从那个梦中醒来了。就象以前奶奶说的,彩衣犯病的时候不打也不闹。只是静静的坐着,眼光呆痴,象放弃了肉体的灵魂在梦中的天国里永不知醒来,也就是所谓的文疯子了。吃喝拉洒都要人照顾。彩衣看到男人鬓角白了,“我睡了,多长时间?”“两年。”两年男人就这样不知前途的伺候着自己,男人老多了。彩衣摸着男人的脸,泪盈双眸,“哥,哥,我对不起你,彩衣让你受累了。” 彩衣看着镜子中的自己,瘦俏苍白。彩衣觉得自己真是有罪。彩衣就不该在世。彩衣觉得她该和小雪做伴去。可是男人一个人也太孤单了。她要给男人留一个后。哪怕她为此死了,她也心甘情愿。她有娘,有小雪。在这个世间如果能有个孩子伴他,相信他也不会孤单。“哥,彩衣对不起你了,哥,你这回就依了彩衣吧。” 彩衣不再吃药。她要清醒一个月,保持一个月,怀个全乎的孩子。她把从男人手里接过来的药全都藏在个衣兜里。一个月,她终于保持下来了。这一个月,她没有让男人近她的身,整整三十天,她把每一天都攥在自己的手心里,攥出汗来。 第三十天的那个晚上,她自动交出了自己。看男人在自己身边畅快的睡去,两行泪止不住的滑了下来、、、、、、 一连两个月,她和男人似乎又回到了日子最初。甜蜜、安定、满足。第三个月,月经没有来,彩衣知道她成功了。男人看着她:“傻呵!你,我不要孩子了。就咱俩好好的过。”“不”,她趴在男人的度量里, “我要给你个孩子,咱一家三口好好的过。” 这一回,老天好象听到了彩衣的祈祷。彩衣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彩衣也还清醒着。看一看天热了,麦子黄了。一家人都去忙着收麦子了。彩衣一个人在家坐着,她想去厕所。她拄着拐棍慢慢走出来。院子里风很静,那棵石榴树也静静的站在院子的那个角落里,这一刻是那么的独特,满树红花,是的,满树的红,红,红,红,满满的红。彩衣抬起头,天空上的云大大的一朵浮在天空上,艳红艳红的、、、、、、 白色的云,白色的云,突然之间天黑下来,大水,漫天漫地的大水,冲过来,冲过来,彩衣飘了起来,又沉入水底,冰,冷,水刺骨的冰寒,冷,冷呵,冷、、、、、、 彩衣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依然窗外的那棵石榴树。她就知道,她又活了过来了。她看见男人手上的那几粒血红的药,她知道她又吃了药,她又返来了,幸福去了又来了。 这一回,不用看镜子,她就看到了自己的新样子。她的双腿新鲜的歪曲着,在地上走路就不再是走,而是晃,摇晃着前移,象个不倒翁。彩衣对这个新的自己并不感到新鲜。每次醒来,都会看到一个新的自己。她不知道这是上帝对她的仁慈依然残忍,每一次都让她醒来,每一次都任意的捏造着她,就象捏造着一个捏造坏了的泥娃娃。可她没有时间悲哀,她要抓紧时间在世,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又会死去。她不想照镜子。她只知道她有了男人,她另有了儿子,她有了一个三口人的家,她有了要好好过的日子。 她也听男人和婆婆说起她的断腿的事,说到她们从麦地里返来看到她浑身是血的倒在院子里,她的那条本来是好的腿扭断在椅子下,血流成为一个小湖,不仅是从断腿处,更多的是从下身源源不断的流出来,她早产了。婆婆一说起这事,就后怕,拍着胸口说,要不是妹妹返来拿镰刀这两条命就都没了。幸亏大人孩子都平安。 其实不用婆婆说,彩衣也能想到自己事先的样子。唉!那不是梦,是真的,是真实的。那满天艳红艳红的云,那流淌在双腿间的大水,那天黑下来时的严寒的刺痛,那都不是梦,是真的,是真实的,是她失去自己的真实。 彩衣不再照镜子。她知道她的样子有多么丑怪。短短的头发,浮肿的脸。这是长期治疗的后果;一条腿瘸,一条腿弯曲着,这是为生这个孩子留的后果。她不怕,再丑她也不怕。她有了儿子。她有了儿子了。儿子一岁了,叫天赐。她想老天真的很残忍,让她错过了儿子的婴儿时代。可是老天也真仁慈,儿子身体康健、聪明聪明。婆婆天天手不离怀的抱着。孩子自生下来就跟着奶奶,和彩衣倒有些生份。这小家伙一看到彩衣就哭。男人不满的在儿子胖墩墩的屁股蛋上亲亲的拍一巴掌。儿子哭了,男人笑了。看着男人的笑,彩衣觉出一种幸福来。 晚上,男人搂着彩衣一脸幸福的打算着,“彩衣,明年咱养一头猪,卖了粮食,我再打个长工,攒些钱给你好悦目一看病,看好啦,以后再挣钱供儿子上学,挣钱给儿子盖楼,给儿子娶媳妇,到时有了孙子、、、、、、”男人一脸幸福的打算着。彩衣看着男人那幸福的样子,她就觉得幸福。她没有男人想的那样远。她也从不敢想那样远。她只要男人不嫌她丑,不嫌她病。她只要儿子康健平安。她只要一家三口人在一路。就这样过着她的幸福生活。 男人果然喂了一头猪,男人还天天出去挣钱。儿子会走了,儿子会说话了。儿子在院子里迈着小步子扭扭的走。儿子奶声奶气的喊:“奶奶,抱抱。”婆婆满脸笑开了花,伸手抱住了儿子,在儿子脸上大大亲了一口。又扭头把孩子递到彩衣怀里,“去,叫你妈也亲一个,看咱天赐真乖。”彩衣紧紧抱住儿子,把脸贴在儿子胖胖的小脸蛋上,想叫一声,我的儿,却又说不出一句话来,倒又流了满脸的泪。婆婆抱过孩子,“这好好的,咋又哭了?”“我”,彩衣又笑了,“娘,我这是高 兴的。” 是的,彩衣是幸福的。男人说年底卖了猪,就去医院。听说那家医院治好啦许多象彩衣这样的人。男人还说比彩衣还历害的都治好啦。“彩衣你一定能治好”,男人看着彩衣认真的说,“真的,我一点也不骗你。”彩衣笑笑,她不在乎好不好,只要儿子好,男人好,一家三口就这样过下去,她就很知知足了。 六 可是,幸福呢? 彩衣觉得她的幸福就象天空上的,白绵绵的云,多美,飘在蓝蓝的天空上多安闲。可彩衣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会变成血红,铺满她的世界。 那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彩衣之后想到来,整个就是乱乱的。那天一大早,全家都会在吃早饭。只有公公说昨夜他在南地下了两个夹子,他要赶早去拿了返来再吃。公公走了有一顿饭时候,一辆车开进院子。车上下来几个人,进门就翻东西,找人。说什么公公欠了乡里的提留款,还和乡里打了讼事,讼事输了。人家审查院的人来执行。还说有钱给钱,没钱就拿东西顶。一时间鸡飞狗跳,婆婆叫孩子哭的。公家人要公公出来,公公早得了信,躲了起来。来人就说躲了和尚躲不了庙,有个执得的就说,和他们说什么,没人拿东西就是了。于是几个人就扛粮食推车子。男人不依了,跳起来挡在粮食垛前说这是他的,爹的早就没了。“什么你的,我的,你们还不都是一家子吗?”执行的人说着,就把男人推一边去,就上去扛粮食。男要急了,扯着声音说:“你们不能扛,这是留着给俺媳妇看病的。”执行的不依。男人就要跟人拼命,死打烂缠的。惹的几个执行的起了火。东西也不抬了,推推搡搡把男人塞小车里,留一句话,“叫他爹拿钱来赎”,就一溜烟开跑了。 之后的事就更乱了。刘家兄弟姐妹都来了,聚在家里商量怎么样托人、送钱、领人。一个家乱七八糟的。之后是妹子出去对彩衣说:“嫂嫂,你看家里乱的。大人小孩都有事。咱娘还得看天赐。这几天俺哥的事,急的她的头发都白了。人一犯糊涂就拿东忘西的。娘年纪大了,别再出点什么事。我把咱娘和天赐都接俺家去过几天。让大弟把你送你娘家过几天,俺哥返来了,叫他去接你。” 彩衣知道妹子说的也在理。她吃喝拉洒都要人照顾,婆婆不在家,一屋子剩的都是大男人,她也不方便。妹子想的也对。人家能接娘和小侄子过几天也就尽了心了。没有连瘫嫂也接已往的道理。彩衣点摇头。 就这样,彩衣回到了娘家。哥和弟都成为家分出去了。父亲一个人搬到厂子里去了。彩衣只能跟着年老的奶奶。看着八十多岁的奶奶艰巨的给自己端饭送水,擦刮刷洗,彩衣的心都碎了。彩衣进门子三天了,嫂嫂和弟媳都没来看她一眼,哥和弟进门点摇头,三句话都没说就走了。彩衣知道这是嫌她。彩衣不恨哥嫂,连爹都没来家看她一眼,她还能怨什么。再说了就是她有话,也找不着个人说啊。奶奶耳背,说了也听不见。自来到娘家,彩衣就不说话了。她只在心里想儿子在妹子家过的可好,她只在心里算男人什么时候出来,好早点把她接回去。她心里最想的依然儿子。想的一晚一晚的睡不着觉。 就这想熬了半个多月。男人来了。那是个阳灼烁媚的下午,男人来了。男人坐在床铺旁,和彩衣说了许多话。之后男人说他得回去了。男人不美意思的笑笑说他从看管所一出来就到这来了,还没回家。男人说家里半个月没住人都该长霉了。男人说他回去就把娘和儿子接回家,他把家好好的拾搡干净,让娘帮着把被子拆洗好。后天他就来接彩衣。彩衣真想对男人说,不,哥,不,我这就走,我这就跟你走。可是彩衣什么都没有说。是的,彩衣知道男人这样做是对她好。男人要把家收拾好啦再把她接回去。彩衣知道男人想的是对的。她回到家什么也不能做。彩衣含着泪答应了。彩衣只对男人说了一句话,“后天,我等你。” 男人摸摸她的头,笑笑走了。男人起身出去了。彩 衣听到男人在外屋和奶奶说了声,“奶,我走了,麻烦事你照顾彩衣”。彩衣听到奶奶的闷咳,听到男人的脚步声出了外屋的门。彩衣透过窗子看到男人走出去的背影。正是傍晚时分,西边红云满天,男人背影在彩衣的视线里被涂了一抹淡淡的红。她看着男人背影有一种如同梦里的感觉。男人到大门口了,男人要出去了,她看到男人后脑勺上猛然绽开了一个独特的笑。她叫了一声,其实她只是张大了嘴,叫声只在她的心里回荡。 第二天,男人没有来。 第三天,男人都没有来。 第四天,大门开了,来了一大堆人。是公公,二叔,队长、、、、、没有男人。他们来了,带来了男人的死讯。说男人回到家,晚上吃了饭还看了电视。一切都好好的,晚饭还吃了两大碗面条。真的,来的人说,还和他爹说天一亮就去接他儿子和他娘去。第二天公公预备好啦接人的车子,男人还没起来。做好早饭叫他吃,人都硬了,床前的地上吐了一大片、、、、、、 “你看一看,你看一看”,来的人说,“真是急症啊!连治也没个机会,这人可真是命苦”。屋子里哭声一片。她没有哭,她早就知道,她早就知道,她想说她那天看到男人的那个独特的笑,她想说、、、、、、可是,她什么都没有说,都没有眼泪,她只是木木的坐在里屋的床上听外屋的他们在说,在不停的说。他们在和彩衣的父亲商量,说她这个样子,丧事参不参加也没多大意思;又说婆婆病了,也没时间照顾她;说她男人没了再回老刘家也没啥意思了;说让程家看着办,以后再嫁再走老刘家也不会说啥;说她、、、、、、 那群人来了又走了,就好象在梦里一样。三天后,彩衣的男人下葬了,彩衣没有能够参加上男人的葬礼。可她看见了葬礼,真的看到了葬礼。她看见男人的棺材在前面走,她在前面哭;她看见儿子被人抱着扶着一个大白幡,儿子哭的小脸都白了。一忽儿儿子又长大了,儿子在叫着她的名字,彩衣,彩衣。一片红,在艳艳的红里,她好象是儿子的新娘,儿子对她说他会照顾她一辈子。 一会儿,到处都是雾。就象在永不醒来的梦里。一朵大大的、艳艳的红云在她前面不远的地方飘着,红云上面坐着她的男人,男人怀里抱着儿子,男人在对着她笑,男人笑着对她喊,彩衣,彩衣、、、、、、 她看见她在前面追着红云跑。她一点也不瘸,她年轻鲜艳,穿一件白长裙,长发及腰,赤足奔跑。她的脚天然鲜艳,详尽纤巧。幸福就在前面,幸福就在前面的那朵红云里,她跑,她跳,她要去追,幸福就在前面,很快她就会追上了,她的红云彩,她的幸福,她要去追,去追,很快她就会追上了,很快,很快,很快、、、、、、 2007年12月29日 下午2点 初稿 2008年5月23日 下午5点 定稿 跋文: 这篇稿子从2007年12月28日起草,到29日完成,写作顺利极了。自己被这篇稿子深深打动,为彩衣的命运伤心。幸福是什么,对彩衣来说,幸福就是天空上的,铺满天空,绚烂夺目,一大朵一大朵,艳红艳红的云。人生如海,太宽太大,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太多太多。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不幸的了,可是那些太多太多的无法想象的苦难,我们其实还没有经历过。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到。直到我们看到别人的悲剧,看到象彩衣这样在世的人,看到在她们的眼里,清醒的在世就是无上的幸福时。我们发现,我们止不住哭了,我们哭的同时也发现,其实,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比起她们,我们其实拥有的,许多许多。(完)这天晚上,在上海浦东陆家嘴的一个工地上,一群民工正聚在一起聊天。单身汉的宿舍,每到夜晚,话题最广:烟酒麻将,男人女人,干活挣钱,养家糊口......这时,只听一个 ..
谁将接任董事长?财产继承有无纷争?“逸飞”品牌的价值,如何得以延续?陈逸飞留下的商业草图需要有人继续描画……文/本刊记者 刘建强一幅商业王国的草图陈逸飞以一个艺 ..
幸福是天上的云相关故事
- 1 人生的快乐和幸福都藏在糊涂里
- 2 被人相信的幸福
- 3 天堂里再不会有幸福的假象
- 4 幸福蜥蜴
- 5 洋娃娃的幸福
- 6 是幸福还是痛苦:帝王如何临幸后宫三千佳丽
- 7 女人,上床越早,离幸福越远
- 8 端午节短信
- 9 第三处错误
- 10 幸福是天上的云
猜你爱看
-

希腊神话30篇完整版
1、尼俄柏希腊神话2、乞丐奥德修斯来到大厅希腊神话3、俄狄甫斯和波吕 ..点击量: 3472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热门15篇
1、彭忒西勒亚希腊神话2、天马与王子希腊神话3、赫拉克勒斯为翁法勒服 ..点击量: 1992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600字锦集
1、美狄亚和埃厄忒斯希腊神话2、赫拉克勒斯和阿德墨托斯希腊神话3、围 ..点击量: 1371 | 时间: 2025-06-02 -

爱情故事100个
1、静候一次回眸爱情故事2、就是这个温度爱情故事3、单车上的爱情爱情 ..点击量: 2379 | 时间: 2025-06-02 -

中国历史故事全文九个
1、中国历史故事:盘点中国历史上那些经典阅兵中国历史故事2、军法始于 ..点击量: 1943 | 时间: 2025-06-02 -

格林童话十个内容
1、金钥匙格林童话2、金鸟格林童话3、蓝灯格林童话4、狼和七只小山羊格 ..点击量: 3219 | 时间: 2025-06-02 -

安徒生童话短篇五个
1、天鹅的窠安徒生童话2、梦神安徒生童话3、飞箱安徒生童话4、大门钥匙 ..点击量: 2500 | 时间: 2025-06-02 -

益智故事完整版1300字
1、顺势趴下并不是屈服的智慧益智故事2、龟兔赛跑益智故事3、认同自己 ..点击量: 1523 | 时间: 2025-06-02 -

罗马神话五个免费
1、狄安娜和阿克泰翁罗马神话2、俄狄浦斯的故事罗马神话3、庇格玛利翁 ..点击量: 1357 | 时间: 2025-06-02 -

历代名女名妓七篇推荐
1、谢道韫临事不乱历代名女名妓2、中国历史上十大名妓之死——玉堂春尽 ..点击量: 1639 | 时间: 2025-06-01
本站名称: 狸猫故事(m.limaogushi.com)
内容收集于网络或由网友投稿提供。
如有侵权请迅速联系本站,本站在核实后立刻作出处理!
Copyright ©狸猫故事 2019-2022 故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