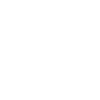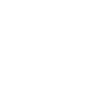最后一问
故事频道: 感人小故事
字体大小
A-
18
A+
阅读: 899次

作者/孟橘昭
聚光灯打在舞台上分外刺眼,台下的一切都黯淡了,黑漆漆的一片,坐了几个人都看不清真实的表情与样貌,只是有严厉的声音从高处穿来,仿佛如来佛祖的五指山徐徐地压向台上的人。
这所有对于宁苏来说是这么熟悉却又那么不真切,只因她阔别了这个舞台已经长达四年,而氛围和开场白依旧如初。
第一问
“你为什么要考中戏?”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从四面八方逼向宁苏。
四年前,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位置,有人问了她一样的问题。而事先的宁苏还很年轻,她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全是自信与满得即将溢出来的热情。
那时候她大声地回答道:“因为只有在中戏我才能更全面地学到全国最为顶级的戏剧文学方面的知识,凭着我对文学的热爱,我也必须要来这儿走一道!”
是怎样的年轻气盛,意气风发才能说出那么义正词严的话,年轻的利益就是初生牛犊(calf)不怕虎,狼(wolf)巢虎穴都敢去闯一闯。
班主任望着宁苏手上的休学申请书,迟迟不伸手接,神情凝重而严厉:“你现在马上升高三了,而且依然班里最有望考上重本大学的尖子生之一,你要是就此疏弃学业,跑去瞎厮闹,再返来的时候,谁也不能保证你是不是还能考上个专科学校啊。”
宁苏固执地说:“老师,我已经是十八岁的成年人了,我能自己做决定了,既然做出了选择我一定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绝食了三天与父母对峙不下,最终依然以父母的妥协作为结尾。
父亲(father)说:“要去你就去……以后要是碰到什么,就别转头埋怨我和你妈,这半年我不会再干涉你任何事,明早我就给你订机票,你赶紧给我走,省得我看着心烦!”
第二问
“你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是什么?”沉默了小会儿,另外一个评委老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就像一个重磅的炸弹,这样的问题稍有一点差池便能让宁苏万劫不复。
宁苏低下了头,叹息了一声,回答道:“我最初对于文学创作的理解不过是以一颗最为真挚的心用文字去挖掘人类心里深处最本质的东西。而现在对于这个初衷我依旧没变,只是多加了一条,文学创作依然作者本身一种肉体与精神双重磨砺与探索的历程。”
第一次坐飞机背井离乡,宁苏看着窗外厚厚的云层镀上一层淡黄色的光晕,那像是就是文学模样,它厚重又深沉令人难以捉摸,但与此同时,它又如此的迷人,令人可以跨越空间与时间的限制,自由地遨游与探索,使人无法抗拒,深受感动。虽然往后的日子无法预料,但心中对于文学的虔诚能够帮她战胜一切困难,虽然那真的是百倍艰巨,艰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宁苏还未从对祖国大好国土的感慨中缓过神,就被抛入了一个陌生又令人大失所望的情况中。
那只是一间小小的艺术培训机构,其范围甚至比宁苏故乡的村小学还要小。一排排用平板搭建的办公室与教学楼,另有一栋孤零零的住宿楼矗立在只有一个游泳池大小的操场边上,另外一间隐没在一棵海棠树后的小型的平板房便是食堂了。
这便是宁苏的第一堂课。她所面临的绝对不只是生活条件上的恶劣,而是来自各个方面的无法协调。这种熟悉并不是浮于表面的,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体会到的就越加的深刻。
和宁苏一样学艺术的孩子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不少是成绩极差又不学无术被逼着无奈才来学艺术考大学的。教授他们专业知识的,多是从中国传媒大学、中心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本科生,也有中国戏曲学院的研究生。
这仿佛应该是令人庆幸的一件事,但事实却是残酷而又伤人的,不管顶着什么样的头衔,骨子里嫌贫爱富,欺强凌弱的本质都是无法改变的。
“同学们学了艺术,以后想要去哪些国家深造呢?是澳大利亚依然美国,有钱就出去,反正在国内也上不了好大学,你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水平。宁苏同学,你想去哪个国家呢?”优雅鲜艳的女老师,温柔地瞧着宁苏。
宁苏低垂着头,脸憋得通红,声音很小,但语气刚强:“我家没钱,我也不想出国,我只想考中戏。”
教室里瞬时鸦雀无声,过后便是一阵轰笑声如浪潮席卷了宁苏。
漂亮的女老师微愣,嘴角抽搐了下,有些不自然地笑了,语气里带了点调侃:“这样啊,那……宁苏同学可得努力了哟。”
又是一阵笑声,逐步沉没了宁苏的声音,她站起身拿着书本走出了教室。
北京已经开始飘起了雪花,望着满天飞雪,宁苏的心冰凉一片,她掏出临走前妈妈塞给她的旧手机,想要给父母打电话,按下了数字,却始终按不下通话键。
父亲的话还在耳边,他说过不会再干涉她的事,这样打电话回去,是要跟他说些什么呢?是要说她忍不住委屈想回家了吗?
不,当然不能这样,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算是打落了牙齿也要和着血吞了。
宁苏将手机塞回了口袋,冲向茫茫大雪之中,严寒的天气,泪水也迅速凝聚了,只有阵阵寒风在不断提醒她保持清醒。
之后再回忆起已往,宁苏只是苦笑,那些忍着泪水的抑郁时光,恰似一颗被深深掩埋在地底的种子,想要破土而出,却不断的被压抑与打击,而心里另有那股子不妥协的韧劲和对文学的虔诚期盼,一向支持着她,细数着在北京的每一个日夜。
第三问
“你家景怎么样?”这是每个艺考生必须面临的质问,家景如何有时侯决定了你是否有资格持续文学的创作。
宁苏停顿了片刻,便扬起了头无所畏惧地看着台下模糊的评委桌:“我家景平平,父母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可他们是善良淳朴的人,像全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慈爱,尽其所能地满足我的一切需求,就算是无理取闹。”
北京的雪,来得过于凶猛,迫不及待地将整个北京城包裹了起来。学校的早间广播起了音乐,是舞动精灵的《far away from home》。
宁苏以为一辈子都不会掉下的泪竟在顷刻间决堤,执拗着一向不肯给家里打电话,可是总是盼望着手性能自己响起,大概一不小心拨通了家里的电话,那也是好的。
再听到父亲的声音,隔着音波是那么遥远,责备语气里藏的是担忧:“你还真没良心,我倒是犯了什么天大的错,你连电话都不打一个返来……我昨儿看了天气预报了,北京那边下大雪了,你要多穿点,特别是你的腿,给我裹牢实了!”
宁苏吸了吸鼻子,忍住了泪水,笑着说:“爸,我错了,我在这边挺好的,你别担忧……”
没有给父亲再多开口劝慰的机会,宁苏仓促挂了电话,她怕再听下去,她会生出就此放弃的念头,然后落花流水地回到故乡。
望着手上厚厚的一沓稿纸,宁苏只能是笑了。
那是她写的叙事散文,被老师们当作足球一样,从一个手里踢到另一个人的手上,到最终它完好无损地回到宁苏的手里,干干净净不染一点墨迹,连日期都不愿给这个穷孩子打上一个。
宁苏在心里默想,谁说我这么久以来没老师关注,就什么都没学到。就算是无人救赎,也得要学会自救。这一课,有谁学得比她更深刻?艰辛的岁月总会已往,并会化作无比巨大的力量,让她乘风破浪,披荆斩棘。
最终一问
时隔四年,再站在这样的面试台上,宁苏依然有些不适应,面试完毕,她长舒一口气,转身预备走出考场,一个老师突然之间之间之间叫住了她。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确实记得你,你似乎四年前来参加过本科的艺术考试,事先我也是面试官之一,我注意到你,问了你一个问题,但是你的回答我并不写意,现在我依然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最终悔的事儿是什么?”
宁苏惊了一下,想到了那年在北京的最终一个月,绝境之间竟逢生气。
她遇见了一个很好的老师,那位老师不盘算她的家景,看到了她的努力,他用尽了心力去栽培她,最终给予了她一定,同时嘱托了她一件事,就是这个美意的嘱托却办了好事,使宁苏与中戏擦肩而过。
四年后的明天,当再次被提及旧事,宁苏已经坦然了。她深吸一口气,慢慢说道:“我最终悔的一件事,是四年前艺考说了一个大话,为此懊悔了四年,我自认从没做过让自己懊悔的事,唯独那一件是追悔莫及的。而我懊悔的不仅仅是我对别人说了大话,更懊悔的是,我不敢面对最真实的自己,这才是最大的失误。”
评委席的方向依然一片漆黑,大家都很安静,想是要听听宁苏的下文。
宁苏接着说:“其实我的腿有残疾,刚刚走出去的时候,老师们应该也注意到我一瘸一拐了。四年前我撒谎了,说是扭到了脚踝。其实是因为我八岁时,出过一场车祸,事先我是一个学跳舞的孩子,很热爱舞蹈,可是车祸以后就再也不能跳舞了,我剩下的精神支柱就只有文学。经过了这些年,其实我懂得了许多,并不是进了中戏就能完成文学梦,不进中戏就一定不能完成理想,仅仅只是我想要去做这件事,主要的是,我为理想奋斗过了。”
话音刚落,掌声却响了起来,宁苏深深鞠了一躬,心中再无遗憾地走出了考场。
花儿说,我要谢了作者/ 陈辉故事发生在一个拉丁美洲的小镇。一个叫乔皮奇的男孩的智力似乎低于平常值,很少有人和他来往。绝大多数时间,他总 ..
向善良的心行礼作者/ 朱成玉一天早晨,坐在的士里,司机一边开车一边收听着本地的一个新闻频道。当时本地发生了一起煤矿透水事故,一共12人被困井下, ..
最新故事大全
去首页逛逛
-

希腊神话30篇完整版
1、尼俄柏希腊神话2、乞丐奥德修斯来到大厅希腊神话3、俄狄甫斯和波吕 ..点击量: 3139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热门15篇
1、彭忒西勒亚希腊神话2、天马与王子希腊神话3、赫拉克勒斯为翁法勒服 ..点击量: 1620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600字锦集
1、美狄亚和埃厄忒斯希腊神话2、赫拉克勒斯和阿德墨托斯希腊神话3、围 ..点击量: 1298 | 时间: 2025-06-02 -

爱情故事100个
1、静候一次回眸爱情故事2、就是这个温度爱情故事3、单车上的爱情爱情 ..点击量: 2161 | 时间: 2025-06-02 -

中国历史故事全文九个
1、中国历史故事:盘点中国历史上那些经典阅兵中国历史故事2、军法始于 ..点击量: 1841 | 时间: 2025-06-02 -

格林童话十个内容
1、金钥匙格林童话2、金鸟格林童话3、蓝灯格林童话4、狼和七只小山羊格 ..点击量: 3132 | 时间: 2025-06-02 -

安徒生童话短篇五个
1、天鹅的窠安徒生童话2、梦神安徒生童话3、飞箱安徒生童话4、大门钥匙 ..点击量: 2148 | 时间: 2025-06-02 -

益智故事完整版1300字
1、顺势趴下并不是屈服的智慧益智故事2、龟兔赛跑益智故事3、认同自己 ..点击量: 1464 | 时间: 2025-06-02 -

罗马神话五个免费
1、狄安娜和阿克泰翁罗马神话2、俄狄浦斯的故事罗马神话3、庇格玛利翁 ..点击量: 1168 | 时间: 2025-06-02 -

历代名女名妓七篇推荐
1、谢道韫临事不乱历代名女名妓2、中国历史上十大名妓之死——玉堂春尽 ..点击量: 1422 | 时间: 2025-06-01
本站名称: 狸猫故事(m.limaogushi.com)
内容收集于网络或由网友投稿提供。
如有侵权请迅速联系本站,本站在核实后立刻作出处理!
Copyright ©狸猫故事 2019-2022 故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