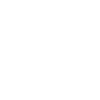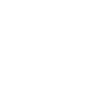邂逅成就了一世纠缠
文/无心 图/赵婷
一、 重逢
又到四月,正是“梅子黄时雨”的时节,不免使人眷恋起水乡的烟波。 “明天,去玩吧?”我轻幽的说。“哪有空啊!等这段工作忙完了,我带你去!”聪笑着,又把头埋进公文中。
本不期待有覆信,但他的回答仍叫我满心失望。我转头看向窗外,雨还在绵绵的下着。细薄的雨飘落在上海这个繁华的都市里,只觉得不应时宜的郁闷;原本,这雨要下在苏杭等地,轻轻柔柔,似絮非絮,才有说不尽的缠绵……
不由得想到在杭州的日子,时常面对一泓碧波,充满相传的西湖,尽管已经事过境迁,仍风流雅致得叫人心醉。到了上海,有了繁华、有了格调,却失却了骨子里的雅致。我,本不属于这座城市的……
第二天,没有通知任何人,留下一张素蓝的纸笺给聪,我一个人,独自出游。
雨,一向绵绵的下着。车上几个年轻人坐在一路,又唱又闹,我只是微笑,在水乡,似乎连吵闹也变成为生活的雅趣似的。
下车,打开油纸伞,静立细雨中,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游客一哄而上,仿佛眼前可口的餐点。偶尔有几个人转头看我,偷偷的嬉笑。我知道,是为了我手上的油纸伞,怕是他们笑我故作风雅吧。我只是笑,任他们笑吧.还在踌躇之际,背后有人猛一撞,一时重心不稳,我马上往前跌去!“啊!”一声惊呼,一只大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腕,往后一扯,我又往后仰跌,落进一个度量中。我反射性的看向度量的主人。那是一张年轻的脸,意气风发的眉毛配合着神采奕奕的眼睛,现在那双眼睛正懊恼和焦虑的看着我:“没事吧?”“没事。”我站直了身,看一看在一跌一扯间掉落在地上的油纸伞,不由得皱眉。
“对不起!”那大男孩也看到了浸在泥浆中的油纸伞,他忙不迭的将自己的伞塞给我,“我赔你!”
我皱着眉接下了。我喜欢雨,但是不喜欢淋雨。但是看着雨飘落在那男孩的头上、肩上,我仍不住的问了一句:“你不怕淋雨吗?”“不怕!”男孩笑着,指指不远方,“我的朋友也有伞!” 他的同伴已经开始召唤他了。 “我要走了!不美意思!”大男孩笑着,招招手,“再见,雨巷姑娘!”
“雨巷?” “戴望舒的《雨巷》!”人已经跑远了,声音还在飘荡。 我怔忡了一会儿,才想到是那首诗。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我笑笑,不以为然。
早晨的游区已经洗去了昨日霪雨霏霏的迷离,朦胧的朝雾中弥漫着淡淡的泥土气息,虽然已经用不着撑伞了,但我仍然撑着我的油纸伞。
再潇洒,也有所顾忌,昨晚,我依然打了电话给聪,也许已经习惯了我的任性,聪只是叹口气说:“好好玩,过两三天就得返来了。唉!”——我有些怅然,在聪的心目中,我成为要糖吃的无知小孩了。从什么时候起,聪已经不能像已往一样,参与我的任性、我的随意呢?也许结婚、也许柴米油盐真的能湮灭人心目中真正的渴望。
“卡嚓”,一道闪亮的闪光,我一惊,惊骇的转头一望。 “嗨!我们又晤面了!雨巷姑娘!”昨日莽撞的大男孩扬着灿烂的笑脸,一如早晨的旭日。我心一动,不由得也微微一笑,看向他手里的相机,迟疑了一下,才问:“你在拍我吗?”“是啊!”大男孩坦然的说,顿了顿,又开口,“我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我默然,又是戴望舒的《雨巷》,我真的是那样吗?“哀怨又彷徨”? “很象专门为你写的。”大男孩补充。
“但是——明天没下雨……” 我轻轻的说,似乎自言自语。 “谁说没有!你看一看!”大男孩笑着,将相机架好,调弄了片刻,抬起头招手,“过来看一看!”
我迟疑了一下,收起伞,走了已往。大男孩让开,我便从镜头里打量着清早的游区——刹那间,我一震,那镜头里的竟是我刚才所见的游区:朦朦胧胧,漾着水乡的雾气,竟如下了轻烟般的细雨一样。我不敢置信的抬起头,又看一看是不是真的下雨了。没有,眼前的游区新鲜明朗的像刚洗澡过的越女一般!
讶异赞叹的神色已经浮现在我的脸上。 大男孩得意的笑了,说:“另有更精彩的呢!来,让我弄给你看。”我让开,看着大男孩在他的包包里拿出一些东西,又是安装又是调弄,一切都那么新奇! “来,看一看吧!”我简直欲罢不能,在他的调弄下,一样的游区,在相机却展露了千万种的风姿:清新明朗的、柔媚迷人的、古高雅致的、阴郁压抑的……
我吁口气,满足的说:“我以为相机是最真实反映事物的,原来不是如此。”
大男孩笑了:“我就是喜欢这一点才学摄影的,只要有各种设备,我就能将世界改变成我喜欢的样子!” “这样子好吗?改变了,也许就不真实了。” 我淡淡的说。
“怎么会!正如你刚才所看到的,怎么改变,变得是外表,不是本质。” “但终究一切都会变的。” 我叹息一般的说,脑子里想着聪专心公文的情景。
“如果这里也像上海一样,矗立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你还会来吗?人的喜爱也许常常变,但真正心里所要的不会变。”
我抬头看他,一张比我还年轻的脸,我微微一笑:“你多大?” “21,明年就毕业了!你呢?” “24。我毕业两年了!”“骗人!”大男孩嚷着,“你看起来比我还小!” 比他还小?我有些可笑:“我干吗要骗你?” “是不是你怕我追你,就用事先用这种借口来搪塞我?”
我一惊,怔怔的看他。他不是开玩笑的!尽管脸上一派轻松,但眼睛的神色却是认真刚强的,他要试探我!我低下头去,心思有些动荡。
再抬起头时,我已经是满面微笑:“要拒绝你,我根本不用找借口,因为……” 我抬起手,“我已经结婚了……”
大男孩怔住了,钻戒冷冷的光芒印进他明澈的眼睛里。他的讶异、失望、尴尬、狼(wolf)狈、甚至恼怒,绝不掩饰的呈现在脸上。
我笑,掩饰了心中失落和怅然,我知道,心底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因为这个大男孩改变了……
游玩之旅结束得很匆忙,像逃跑一样。那张年轻的脸、那挺拔的身影,另有那欲言又止的双眸,像是追捕我的猎人(knife),我没有办法只有逃避。
离开那天,天依然下着雨,但那是倾盆大雨,铺天盖地,我娇弱的油纸伞抵御不住这般凶猛的雨,我只得撑起那天他塞给我的赔罪的伞——鲜白色的,在雨幕中分外显眼!
车要开了,众人已经上车了,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外面的世界是如此不分明! “呀!”车门处响起惊叫声,“你这人怎么搞的……”
我看向门口,还没等看出端倪,一个人影像风一样冲到我面前。 我仰头看他,一身的水,他涨红了脸,嚷道:“我也要回上海。” 我叹息,说:“坐下吧。”
有些事,明知是错,明知是堕落,却无力抵抗……
我看像窗外,雨依旧铺天盖地的下着,外面的景致怎么也看不清,只看见冰凉的玻璃上映着我们的脸:那样亲近,又那样的遥远……
我们没有回上海,在上海转了车,又到了其他地方游玩了。 在异乡,我们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情侣。
因为回到了上海,一切依旧……
二、风云
窗外,大雨滂沱,密密的遮住外面的夜景,只有闪烁的光芒在水光里流动,诡异而艳丽。
窗台上,鲜艳精致的玻璃瓶里,一丛丁香在怒放,清雅的紫色小花在柔和的灯光下分外动人。
我从来不知道丁香也可以像玫瑰那些花一样,可以成束的出卖,而且被修饰的如此娇柔,在晶一般的玻璃瓶的衬托下,美得无法形容。
那是送给我的,是一个无名氏送的。从我返来后,每到丁香的花季,就每日有一束丁香送上门来。
聪曾问过我,我只是淡淡的说:“不知道。”也曾很小心的向花店送花的小弟打探过,小弟也摇摇头,说:“不知道。”——但是,怎么可能不知道!单是看我收花时那种复杂的神色、我看着丁香那种若有所思的样子、另有……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他狠狠的盯着我,狠狠的抽着烟。 “吃饭了!”我柔软的声音传来。
他摁熄烟,走了已往。挨近我,他看见我的眉梢一皱,不落痕迹的避开他——他知道,我不喜欢我身上的烟味。 两人默默的吃饭。
一会儿,他开口了:“迩来我比较有空,我们去周庄,好不好?” “不要了!”我迅速否决,抬起头来,虚弱的笑笑,“我不想去,那里没有什么好玩的。”“但是你一贯不是喜欢一些古旧的城镇的吗?”他端详着我的神情。 “古旧的城镇不止周庄一个。”“我倒想去看一看。听我同事说,那里景色不错,最适合……”他顿了一顿。 我平静的抬头看他。“最适合来一段浪漫的恋爱!”他笑着,“你不想去体验一番吗?” “你要说什么?”我依然很平静。
“我说什么了吗?”他冷笑,“依然你心里有鬼,不愿意我提及?” 我不说话了,静静的扒饭。 他扔下碗筷,冷冷的看着我,心里的怒火高涨:“不分辩吗?”“我能说什么?”我也冷冷的看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象我一样/象我一样地/默默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咬牙切齿的念着,嘲讽的说,“何不谈谈这个‘冷清、凄清、又惆怅’的男人呢,丁香姑娘?”
我霍然起身,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你偷看我的东西!” “我是你丈夫,我没资格看吗!”他冷笑着。
“纵然是我丈夫,你也不能侵犯我的隐私!”平素温柔优雅的面貌全不见了,我浑身颤抖!
“隐私!”他也站起身,“不安于室就是你的隐私?!这些就是你的隐私?!”他手一扬,将放在身上大半天的浅紫色小卡片扔到我身上!若不是一时好奇,他不会去开启我的抽屉,也就不会发现这些令他肝肠寸断的东西!
我看着撒了满地的卡片,那些原本夹在丁香之中的不具名的卡片,——龙飞凤舞的字迹、戴望舒的《雨巷》、影象中神采飞舞的面孔……
“无话可说了吗?”聪冷冷的声音在耳边反响。 “你要我说什么?”我木然的看着他。
“我要你说什么!现在是谁做错了,为什么你还这么义正词严!”他的声音变得尖锐,“我一向拼命的工作,你以为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想给你最好!你居然这样对我!”
“我从来都不要这所有!”我平静的说,“我要的只是在大学时能和我一路分享理想的聪。”
“哈!”他狂笑,“没有这所有,你能有理想吗?你能在窗边看雨、看朝云夕雾吗?我放弃我的理想是为了什么?我让你保有你的理想,你居然对我说这样的话!”
我坐到椅子上,一句不说。我能说什么?始终理亏的是我…… “为什么不说话?”他凶神恶煞的瞪着我。 “我们……”我幽幽的说,“离婚吧!”
“什么!”他脸色变得更为难看了,“你以为你永远如此称心如意吗?我不会答应的!” 我静静的坐着,不再说什么。
他狂躁的瞪着我,我却无动于衷。他循着我的眼光望去——那丛紫色的丁香!他大怒,马上走已往,一扫,玻璃瓶掉到地上,收回清脆的破裂声,碎成十几片;他不顾玻璃割伤的危险,一脚踏上去,拼命的蹂躏着那楚楚可人的丁香花,示威的瞄向我。
我冷漠的看着—— 他气一泄,悲哀涌上心头,真切的知道,那一刻,妻子的心已经远离他了……
大雨一向下着,密密的遮住外面的景色,偌大的空间只有两人的呼吸,和不可言传的疏离……
三、爱你
景物在飞逝,我看着窗外:外面景色明媚,带着苏杭独有的娇嫩和新鲜。
我下意识攥紧手上的字条,心里是张皇的。从来没有意识自己是这样的疯狂,为了一次重逢,我居然可以抛弃曾经深爱过的丈夫,到一个对自己相当陌生的地方寻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男孩子!也许第一次见到他灿烂的笑脸,我就已经疯了……
我恍模糊惚的笑着,竟像回到了年少时,心里忐忑不安又兴奋不已。
到了苏州,阳光依旧灿烂,竟又飘起了细雨,细细点点,如金丝银丝在空中交错,明丽的叫人移不开眼光——原来雨也可以这般灿烂……
“你找棠啊?”面前的老妇人不住的打量我——我知道这个妇人是他的母亲,但一时竟不知怎么介绍自己,只好谎称自己是同学。——“他还在店铺里忙呢!”
“店铺?”我问,“他开店吗?”
“怎会呢!替人打工而已。不过那是苏州城挺大的一个相馆了。”老妇人笑着,“他很忙的,那个照相馆都靠他呢!老是忙得不返来过夜!唉!”——随口里唉声叹气,脸上却掩不住的得意,也许这就是母亲的幸福。
我也笑了,想着那段日子,他老喜欢拿着相机替我拍照,照我的喜、我的哀、我的愁、我的乐……
拿着他母亲给的地址,往他工作的地方而去。忍不住在心里理想着他见到我的模样,该是惊喜吧?那种纯粹的喜悦一定显明浮在他的脸上,毕竟他是那种掩饰不了心里的人!我笑着,甜蜜而幸福的笑着……
果然如他母亲所说,那照相馆很大,是一个很现代化的那种艺术影楼。很难想象,那个喜欢按自己意愿拍摄景物的大男孩会替人拍出如梦如幻的、甜蜜温馨的婚纱相片!
“接待到临!”门口的小姐甜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 “你好!”我有些不安,“请问贺棠在吗?” “你是——”
“以前在上海的同学!”——照旧用这个谣言。 “哦!”小姐漾出鲜艳的笑脸,“他正在替客人照相呢!我带你去找他,请往这边走!” “谢谢!”
越挨近摄影室,心就越发慌了,他见到我会怎样呢?真的会惊喜吗?毕竟那段重逢已经已往好久,自己来找他真的明智吗?真的应该吗?
“他就在那儿!”小姐笑着指着远方,“他在工作,等会儿,好吗?” 我点摇头,静静的凝视他——
“恍如隔世”,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眼前的他仿佛已不是我重逢的大男孩,他已经摆脱学生的青涩,举手投足之间如贵族般的优雅成熟;但他的笑脸依旧,那么灿烂、那么纯真,就如在曾经那样叫我心动……
他结束了一段落的拍摄,新郎新娘去易服服。 我扬起笑脸,刚要开口叫他,蓦然,我的笑脸凝住了——
旁边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子跑到他身旁,细心的替他抹去额际的汗水,言笑晏晏;他对那女孩儿笑,温柔而灿烂的笑;两人言行间说不出的亲昵甜蜜,说不是情侣,谁相信!
我眼前有些浮动,是幻境吗?是做梦吗? 原来——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走出照相馆,阳光灿烂的有点刺目,雨丝还在飘,人群笼罩在金丝银丝之间,是如此疏离、如此不真实;我还在梦中吗?这所有是真是假?
“你们熟悉多久?你熟悉他多少?你爱他什么?居然抛弃我为你奋斗的一切!”——聪痛彻心骨的呼唤招呼——原来我也伤他这么深,可以心痛不知道究竟是那儿痛了!
“我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我飘过/象梦一般地/象梦一般地凄婉迷茫。”——这是他念的《雨巷》,他想象中的我——是啊,我一向只是个梦,是人总会有梦醒,总会有厌倦遗忘我的时候!
“象梦中飘过/一枝丁香地/我身旁飘过这女郎/我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汜的篱墙/走尽这雨巷。”——原来……原来……戴望舒已经通知我了,他终究离我是远了远了……若雨巷走尽了,我另有什么……
我猛然抛下手上的雨伞,蹲在路旁尽情的宣泄我的悲哀、我的心痛…… 管他谁看,本来我已经疯了,在上次就已经疯了……
原来一时的重逢,已经让我爱的如此之深,深入心骨……
四、雨巷
春天的杭州,是柳绿花红的,鲜嫩的绿色和醉人的殷红,另有熏人的暖风;难怪南宋的君主都不思故土,都愿沉醉在这温柔乡之内了。
回到了杭州,虽然躲不了父母担忧的唠叨,但可以面对那一泓碧波,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也许在西湖碧波的洗涤,我终于一天会忘了已往的伤痛与悲哀。
洗干净了手,束起长发,换上紫色的长裙。——我另有一个约会,我的前夫约我。
对于聪,我一向愧疚的。我的任性、自私曾经给他带来极大伤害,但他仍不计前嫌,只是自己不懂得珍惜,错过了就无法再转头。 “我们去哪?”坐在车上,我问。
“去看摄影展。” “你什么时候对摄影感兴趣?” “近段。”聪转头对我笑笑,“去到你就知道了。” 我笑笑,没有说话。
“到了!”车停下来,聪推推昏昏欲睡的我。 “哦!”我起身,钻出车外。 “雨巷艺轩”——我微微一怔——曾经,有一个大男孩,他叫我“雨巷”……
“出来吧。”聪唤我。 “哦!”我收敛心神,该忘记的依然让它已往吧。
这个艺轩相当大,玻璃的大量使用使它明亮清爽;主人放置相片也很别致,似乎心不在焉的随意摆置东一个台子、西一个台子,上面大小不一的放着相框。
“这些摄影作品怎样?”聪问。 “我不懂摄影,不过摄影是很正视光芒,他喜欢在不同光芒下拍摄同一件事物。”
“你看得很仔细嘛!”聪笑道,“你知道为什么这间摄影室叫做‘雨巷’吗?” “为什么?”
“因为这位摄影师因为一幅名叫‘雨巷’的相片而成名的。”聪指指内室,“跟我来!我带你去看一看摄影师的成名之作。”
我笑笑,一点也不意外聪熟悉主人——聪历来社交相当广。 跨进内室,我一怔——全室只有一幅相片,险些象一面墙那么大的相片!
那张相片上,一个紫衣女子,手持一把油纸伞,眼光迷离的望着前方,我脸上的神情是哀怨又彷徨的;我的身边浮动着淡青色的薄雾,笼罩着我,笼罩着我身后的古镇。
——那是我的相片!我在周庄的相片!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我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我霍然转身,站在我身后,不是聪,而是——他! “你——”我愕然! “为什么不问清楚我就走了?难道你一点不想知道那个女子是谁?”
我低头,突然之间笑了,是谁要紧吗? 见我笑,他倒忍不住了:“她曾经是我的女朋友;如果你现在依然别人的妻子,她可能就是我的妻子了!”
“为什么和她别离呢?” “你不晓畅吗?”他叹口气,“那你为什么离婚?”
我看着他,静静的凝视他,蓦然我笑了,甜美的笑脸在我清丽的脸上漾开——我不想问得太清楚,不想知道的太清楚——只要知道我爱他就可以了!
他看着我,蓦然抱我入怀:“若不是我忍不住找你,那我就永远不会知道你离婚了,永远不知道你在杭州,永远不知道我可以这般拥有你!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
我不出声,泪盈满眶,原来幸福就在转瞬间,原来我差点就错失了幸福! 一时的重逢,一时的偶然,也可能是一世的眷恋、一世的纠缠……
这个季节,所有的故事都像风吹过麦地,掀起阵阵波浪。风继续往前吹,麦子留在原地等待成熟的到来。不知道风会不会记得曾经经过的麦地?而麦子是否记得曾经过往的风? ..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 …… “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 四百年来,我终日形容枯槁,幽魂不得安附。冥冥中,我参悟生死抑或仙灵人 ..
猜你爱看
- 1 折翅的千纸鹤
- 2 女孩与发夹
- 3 痴情绝症
- 4 蜻蜓的眼泪
- 5 这个平凡的男人是我的
- 6 交换世界
- 7 美女口述:给我幸福的男人是个可爱的胖子
- 8 合租(微型小说)
- 9 爱情密码
- 10 男人如何回答女人常问的经典问题
-

希腊神话30篇完整版
1、尼俄柏希腊神话2、乞丐奥德修斯来到大厅希腊神话3、俄狄甫斯和波吕 ..点击量: 3473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热门15篇
1、彭忒西勒亚希腊神话2、天马与王子希腊神话3、赫拉克勒斯为翁法勒服 ..点击量: 1994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600字锦集
1、美狄亚和埃厄忒斯希腊神话2、赫拉克勒斯和阿德墨托斯希腊神话3、围 ..点击量: 1371 | 时间: 2025-06-02 -

爱情故事100个
1、静候一次回眸爱情故事2、就是这个温度爱情故事3、单车上的爱情爱情 ..点击量: 2380 | 时间: 2025-06-02 -

中国历史故事全文九个
1、中国历史故事:盘点中国历史上那些经典阅兵中国历史故事2、军法始于 ..点击量: 1943 | 时间: 2025-06-02 -

格林童话十个内容
1、金钥匙格林童话2、金鸟格林童话3、蓝灯格林童话4、狼和七只小山羊格 ..点击量: 3219 | 时间: 2025-06-02 -

安徒生童话短篇五个
1、天鹅的窠安徒生童话2、梦神安徒生童话3、飞箱安徒生童话4、大门钥匙 ..点击量: 2504 | 时间: 2025-06-02 -

益智故事完整版1300字
1、顺势趴下并不是屈服的智慧益智故事2、龟兔赛跑益智故事3、认同自己 ..点击量: 1523 | 时间: 2025-06-02 -

罗马神话五个免费
1、狄安娜和阿克泰翁罗马神话2、俄狄浦斯的故事罗马神话3、庇格玛利翁 ..点击量: 1358 | 时间: 2025-06-02 -

历代名女名妓七篇推荐
1、谢道韫临事不乱历代名女名妓2、中国历史上十大名妓之死——玉堂春尽 ..点击量: 1640 | 时间: 2025-06-01
本站名称: 狸猫故事(m.limaogushi.com)
内容收集于网络或由网友投稿提供。
如有侵权请迅速联系本站,本站在核实后立刻作出处理!
Copyright ©狸猫故事 2019-2022 故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