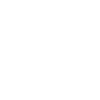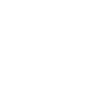你要路过 我要暂过
写一个关于上海的小小说

一向喜欢上海,而且喜欢的有些盲目,其实我从来没去过,我是许多地方没去过,我习惯了纸上的旅行,那么就让我这个纸上的旅行家带各位走上一程吧!虽然路是有点远,你们对我另有嫌疑。
可是有什么干系,你们是你们,我是我,我们辨别找我们所欲望的吧!
从黄浦江上,在1937年的水边,宁静饭店就高高的站在那里,象一个踏着高跟鞋的女人。
但是现在我们再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老了。
现在,那个现在,什么现在。
你以为是拥有了现在了吗?
现在只是个假定,假定你在某个时候拥有某样东西而已。
宁静饭店是二十年代造起来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哥特式修建,她是外滩最早兴建的大楼,她是远东战前最豪华的地方,有一些很老很老的日本人还会提起她,他们闭上眼睛,象是回忆一生中最主要的女人一样。
那楼上长长的甬道,安静的,温暖的,被黄色的青铜壁灯照亮着,两边的房门有时候打开,走出一个三四年代的人,女的比如是恩雅,男的比如是岑寂。女人常着前面有一根抹筋的玻璃丝抹,男的抽着时髦的埃及香烟。
现在我们看到吴宇森的《宁静饭店》,其实讲的是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时代会例外,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我喜欢他们爱欲哀愁的眼泪。
岑寂之后死在上海,那一年死的人太多了,他永远的躺在上海虹桥的一块墓地里,象他的名字,他的周围另有许多和他一路从法国返来的老朋友,既然他生前老是想念着自己该是个法国人,他该满足了。只是他的墓地用冬青树围起来。绿色的藤蔓沉没了他的墓碑,墓碑用的是很普通的石料,名字是简朴的玄色刻的。——他毕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你要路过 我要暂过 (二)
歌要听周璇的,电影要看阮玲玉的,城市的功能就是使每个人的爱好都相近。
岑寂坐在咖啡屋里,跳针是柔蔓的,一圈一圈的转着,偶尔碾到密纹唱片上的细尘之上,扑扑的响,这声音在好久以后只留下“小燕子(swallow),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幼稚园的孩子进行大合唱正符合。
简简朴单,轻轻巧巧,历程中许多的东西会被省略。
恩雅说:我现在走在东山的小巷里常常会反响自己的一生,而也许我的一生就象这一条小巷,暗的路灯,暗的光,人走在里面,象剪纸贴在上面。却很自然。小巷有个新鲜的利益,不管它是建的多新,多晚,很快的它就古老,象我眉间的鱼尾纹。但是我依然喜欢一圈一圈的走着,象留声机上的那一张老唱片,忘了通知你,那个留声机是束缚后的东西,也是上海出产的,很粗笨,耐用。
在小巷的终点,有一张竹椅。竹椅上有个老人,光芒越过屋檐停留在她的脸庞。她的眼睛半睁半闭的和小巷说着私房话。小巷也许在听,也许不再听。也许。
岑寂的眼睛看着咖啡馆的外面,这时一个小姐走了过来。
咖啡馆的下午很安静,除了偶尔的一阵枪声,墙壁上面有一张名媛的月份牌。
“盐汽水”那个瘦瘦的小姐推荐道,她穿着齐膝的改良旗袍,披着一件短而窄的家织开丝米毛衣,她留着一头老式的短发。她看着岑寂的不置可否,她说——荠菜肉丝加年糕也不错,大概是五香茶叶蛋加豆腐干。当然也有咖啡加蛋糕,恩,简朴的日本菜。”
小姐之所以说那么多话,是因为岑寂明天刚好带齐了上海小开的三件宝——怀表、皮带、皮夹子。
“世界上有谁不知道上海”,这是欧洲人当年在上外洋滩挂出来的横幅。可是现在我们只看到老房子上面的烟囱鲜艳无用的竖立着,有法国式的、英国式的。黄浦江仓促的流水带走了尘土上的故事,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岑寂站在江边,一双雪白的手套上包着一封信。
岑寂的口袋里另有两张去香港的船票,现在什么都不值钱,除了黄金和美圆。他自从留学返来一向在一家英资银行上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熟悉恩雅的。
上海的某个平安夜的的前一个晚上,宁静饭店的顶层的一个舞厅,室内华灯缀满,今宵不夜。
据上海档案馆资料:
租界时代——跳舞原为西洋人习俗,他们认为跳舞是一项高尚正派的娱乐运动,除了须领执照以外,无其他限制,亦无其他的捐税····
敌伪时代——这个时期的舞厅特别的繁荣,其原因因为上海的人口畸形的增加,伪政府的腐败,投机的盛行,一般市民在生活上糜烂,莫不以舞厅为社交场所,此乃舞厅的黄金时代而失去了真正的高尚意义。
你要路过 我要暂过(三)
恩雅说:如果我们习惯了回忆,习惯了回到已往,那么你永永远远的活在已往而且活下去,那也是一件很好是事儿。
她沿着淮海中路走着,他的目光追伴伴随着她高挑的身材,她遮住了他所有的世界,自从那个平安夜过后。
淮海中路四周有老牌的西点店,百货大楼。走累的时候,左边是一家咖啡屋,右边是一间电影院。冬天的阳光从矮小的梧桐树的秃枝上照下来,街边的每个路灯列队整齐的象士兵,行人的皮鞋很亮。毕竟淮海中路就是上海的脸面,像纽约的第五大道,东京的银座,巴黎的香榭丽舍、彼得堡的涅瓦大街。
有时候我们幸福的生活在其间就会忘了把这些感受珍而重之的收容起来,当年越洋而抵上海这个全世界公认的冒险家的乐园的欧洲人们在一封封寄往故乡的信中是何等的热忱,描述着我们熟视无睹的历史,比如一九一四年,洋泾滨被填成爱得加路,我们呢/现在只知道延安中路,比如第一家跑马场正式营业,比如从美国来的剧作家整天躲在一间永远拉着白色丝窗帘的房间里写着上海,比如多年后外国人拍的一部《上海大饭店》。
一个是留学返来,事业有成的英派青年。
一个是罗敷有夫,朝九晚五的女职员。
岑寂穿着一件深色的西装,另有白色的长裤和镶拼皮鞋,一脸的机灵、时髦和温顺。这是她现在仅能保有他的唯一印象。她拼命的捂住自己的胸口,担忧着自己有一日会忘记。
他在信中通知她,他现在正学着骑马,那是一项很好的运动,虽然费用是很贵,但依然想看一看她骑马的模样。他甚至有一次忍不住要通知她,他开始学饮酒了,虽然没几口,他又会醉,又会吐。他天生对酒就有点过敏。
一九九二年。宁静饭店被世界闻名饭店组织接受为世界最闻名的饭店,中国只有这一间饭店得到这个称号。
恩雅作为一名现在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老职员,她接到了一张观礼的邀请函,当这张邀请函辗转的到达她手上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后的事儿了,可是有人记取自己也是一件开心的事,她哭了一个晚上,她知道自己白发苍苍,流着泪的样子很难看,岑寂要是当初想到自己到老会是这个样子,还会不会每日信一封一封没有落款的来。
我要路过,我要暂过 (四)
在写之前先感谢一下天骄,以下是他为我提供的更正。
淮海路初建于1901年事先名为宝昌路10年后改名为霞飞路.1949年为怀念束缚战争中闻名的淮海战争改名为淮海路.淮海路旧时属法租界街道宽直修建讲求艺术马路两侧均植法国梧桐树极具欧陆风情。
恩雅那时候心里会笑着男人的心思真是简朴,明明是情书,可是千绕百折的,从最近的永安公司的股票、多伦多路是改建到国联的最新动议,然后象一艘从宁波一橹一橹摇弋到上海的码头的船,淡淡的说及自己的最近,最近又是许多许多的日常琐事,比如开门接报纸的时候在门口跌了一跤,查找着自己的伤口,又说起拜耳药厂的药,药的功效。
恩雅现在会想,我和他其实也就几面,甚至有印象的也只是一面,现在能想到来的岑寂是信中的岑寂。象他自己在信中说的,他现在一个人住,家里人全去了南京,一个人住在麦阳路(现在的华亭路)的公寓里,秋天里这一带非常安静,安静就是一种美,推开窗子或站在阳台上,灼烁着的瓦面。低头看着下面,是那些外国人的小花园,一间一间的。小花园里有着玫瑰或其他植物,说的出名字说不出名字的,围着小花园的是铸铁的栏杆精致、欧化、老派。
岑寂每日回家,之前是转个楼道,楼道通通的发着木板的声音,走进一个电梯里,匡匡的一阵响,就把他提了上去,掏出钥匙,推开厚重的门,在衣架挂上自己的帽子和大衣。
岑寂的酒有点醒了,睁开眼睛,一切依然有点蒙蒙笼笼的,他伸手用力想抓住什么,让自己可以站起来,于是一个柔软的身体跌进了他的怀里,从她背后的镜子的他看见一个女人高高倌起的头发,鬓角露出没带耳环的小小的耳朵,象一个小小的防空洞。那女人一把把他推开,转过头来,岑寂看见了她那艳丽的太过的眼睛。 岑寂见过各种各样的女人,无论的法国依然上海滩,更况且打着领带在上海滩做事象他这样虽是不喝花酒,可是划着拳头,捏着粉头,摸也摸过,香也香过,不稀罕的。而母亲的每个月在南京所做的所能做的也许就是为自己物色儿媳妇,隔有些日子,照片厚厚一叠一叠的塞在楼下的信箱里,小家碧玉、大家闺秀、财阀名媛,美女他算见得多了,可是岑寂的心里依然咯噔的响了一下,象他有时睡过头仓促出门跑步下楼的时候的声音,空洞洞而又有着动静。 这是个供客人小休的小客厅,开着灯,但依然暗。就镜子也让人觉得象带了水气,镜子旁另有一个西洋的烛台,雕刻的斑纹有着弧线的美。烛台旁有一本很厚重的精装书籍,翻开着,是德文。
我要路过 我要暂过(五)
岑寂接过恩雅手上的醒酒的龙井茶,其实他特别怕龙井的味,隐约的有鸡汤的鲜味。
“麻烦事你了。”岑寂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恩雅的头上隐着一缕双妹牌生发油涩涩的香气,迢迢暗渡到了鼻尖。
这个平安夜的前夜他想着自己无处可去,怕堂子里的热闹,就应了他的上司,一个严谨的德国人施笃姆先生的银行同仁聚餐的帖子。出门的时候风就大,又不能象穿长袍的笼着袖子,一进门头晕晕的,到了顶层,施笃姆先生握着他的手,恭喜你,Mr.冷。刚好舞池的曲子播完,全场静了下来,施笃姆先生宣布了他即将升任主管的新闻,最后用冷冷的口气表演着德国人的幽默——在未接到正式的聘书之前,等待是需要,当然一般来说人生总是令人失望,想到你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不如意事儿出现的概率,恩,有八九七十二种可能。 喜出意外,岑寂还来不及表达自己的谦虚,比如他该是只猴子(monkey),有着七十二变才能应付,同事们有真高兴的、假高兴的早团团的围住他。酒一杯一杯不知高低的到了肚子里,岑寂才想到自己已经喝的太多了,而且是法国莱茵河窖藏百年的葡萄酒,后劲比后母娘还厉害。 最终他给扶进这间房子里。
恩雅回答自己也是这间银行的职员,是存档室的。岑寂说着我说呢。话象是要从扑满里倒出钱来一般的不易,辛苦的前胸后背一阵阵的透着虚汗。
一晚间不安稳的睡去醒来,岑寂说着你回去吧。恩雅却是不敢,施笃姆先生交代她的时候,就因为她是结过婚的。她倚靠在一边的案几上打着盹,几次听着岑寂呻吟着一个女人的名字,恩雅有时候会想着岑寂心里的那个她和自己到底是谁重些,这答案也许只有岑寂知道了,可是有着这个念想让她好久以后一想到这个晚上,就觉得温暖,象坐在火炉子的旁边喝着酒,一小口,一小口。
事件:
八一三事件——日本为侵略中国而在上海挑起的军事进攻,因发生在1937年8月13日,故称之。
1937年8月9日下午五时半,日本驻沪水师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带一水兵,驾军车冲入上海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中国军队击毙,日方以此为借口,蓄意扩大事态,对上海发动进攻,日军一方面威胁中国,要求撤离上海的保安队,拆除所有的军事防御工事,并向日方道歉并处罚当事人,另一方面迫切向上海调动两个师团的兵力,同时也将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30艘军舰聚集到吴凇一带,13日,日本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日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炮击,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下令果断反击,凇沪抗战开始。14日,中国南京政府宣布《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迫不得已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中国进入了全国性抗日战争。
你要路过 我要暂过 (六)
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如何度过才不会太长久或显得冗长。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自足的说着,我活够了而不是垂头呆呆的抚摩着床沿象一个已经结了帐却恋着客栈不肯离去的旅客。
恩雅一整天慌里镇静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忙些什么,当日军在炮声隆隆的在闸北响起的时候,大街上的人群们象是被水淹了巢穴的蚂蚁(ant),大家知道,这一次日本人不会想六年前那么顾忌,各个外国租界前巡捕房的警察一切出动,手执着警棍和水龙。
空袭警报一声声的响起的,施笃德先生在宁静饭店召集所有的银行职员,通知大家鉴于目前的形势这间英资银行将退出上海,他个人也将取道香港而回德国。说到这里,他自己心里也在叹气,这座鲜艳的城市明天不知道会如何,只是以他现在的身份,什么都不能明言。(一)聚会会议结束后,施笃德留下所有银行的初级职员,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叠船票,是德国商船的船票,现在上海的海陆空交通线已被日军重重封锁,而南京政府战和未决,便想决战,也不会在这里孤注一掷,日本人谋求一战的目的是如此的显明,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全都垂头丧气的晓畅保卫大上海只是一句空头支票,况且自东三省失陷以来南京政府显而易见已经开习惯这种支票。德国做为日本的盟友,这样的一张船票不吝千金,况且是两张。
——各位先生,很遗憾,这是我个人力量所能做到了,我会记取和大家相处的这段日子,每个人之所以吊唁一个地方,我想是因为那里的人和事,我会记取上海——china。
施笃德走到每个人面前,拥抱、握手。
岑寂在下楼的时候看见恩雅抱着一叠挡住了脸的黑皮精装的帐本仓促的走上楼,旗袍下摆紧紧的缚住她的身段,象鱼鳞和鱼互为表里。他不由的想到事先一位闻名诗人流传的一句——“我要有你的度量的形状,你往 往溶于水的线条。”
岑寂张了张口,想叫住她,却一时间想不起她的名字来。
这时,脚下地动山摇的一响,从窗口望出去,是一大群日本的战机象蝗虫(locust)一样的啃住宁静饭店之旁的一家英国人开的医院。——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日本现在更象一个刚刚长大的孩子,有着比正常大人更旺盛的精力,他已经失去试探的初心,失去的应有的节制,这将导致他最终的失败,这是岑寂写给恩雅信中的一句。
恩雅艳丽的眼平滑过他的面前,象鱼滑过了水。
恩雅下班的路上,街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喧闹,阳光高高的下来放肆的侵夺着每个角落,更加深了这个城市的寒意。她平日常常光顾的水果摊点也全东倒西歪的撇在那里,象离散了父母的孩子。
注:(一)施笃德在香港做了长久的停留后于1937年9月底回到德国首都柏林,任一家私人军工厂的采办,1945年苏军攻入柏林的前夕,象岑寂一般在街上为流弹所中,终年54岁。
(七)我要路过 你要暂过
“依然你的信?”一个报童在路口的转角处拦住了恩雅。这半年来,恩雅已经习惯了他的出现。
不远方的一辆小汽车里,岑寂望着恩雅吃惊的脸庞,想着自己曾经辜负的那个女子,那个女人手温润的能握出水来,想着那个女子的泪水。
船徐徐的驰出了上海滩,江水浑浊,在明亮的夕阳下安稳着每个离去的人的回忆。
恩雅一个人怔怔的站在栏杆上,看着江面上的光晕一圈一圈的漾到自己的眼前,慢慢的眼眶红了起来,鼻尖也痛快的淌出清涕。她的眼泪也引出了更多同船女子的哭声,每个人的目光都遥遥远远的围住上海,昨夜每个人梦里有着繁华,只竟如了烟花,只竟如了小孩子手上的冰棒,好日子是过的那么的不坚牢。 恩雅的丈夫张建从船舱里走了出来,手轻轻的抚摩着恩雅的背,恩雅整个身子微微的一缩,肩胛骨向上一耸。
张建柔声的道:“你不舒服。”他的上海大华纱厂的首席会计师,前几天正为船票奔走,头发也白了好几根。恩雅的船票虽然使他多多少少有些猜疑,真有个那么美意的亲戚,可是此次能得出生天,已是侥幸。兵凶战危他是眼见的,人命如蚁他也是眼见的,只惭愧一贯说过的大话。 张建说着风大着呢,出来吧,你也是第一坐船,也难怪。又说老说要和一路坐一次船,却没承想是一道逃难来着。
恩雅想着亏的他,亏的他这般的挂我在心上,我是怎么当的起,他就只有两张船票的,却全给了我。他心里也该有想着和我一路走的,可他要真问我的时候,自然我是不会答应的,可他也该问一问我。她心里这刻千叨万絮,念念在心的就是岑寂了,却才发觉的他的名字还涩的慌,便在心里也喊将不来。
可是我也只在这刻里挂着他,只因了他对我的恩义,我竟是个俗气的女人。恩雅想。
恩雅“恩”的一声,我不舒服,随口间这话也在她唇间滚了两遍。
黄浦江上正走着一船的回忆。
徐徐的。
我不想十八年去等一个人,一个一辈子也唤不回的人。我轻轻地笑着,拔出了他的剑……1我站在大明湖畔。我听见娘在叫我“虞、虞”。娘说,你叫“虞”,你的生命中有一个男 ..
常言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可生活在G市爱心花园A幢301室的单身汉张君的钥匙却也能打开B幢301室的门。一把钥匙能打开两把锁! 这样的事绝无仅有,也许是生产厂家出错的吧。 ..
猜你爱看
- 1 我不做你的寂寞虞姬
- 2 大龄女倾诉:恨嫁女人不快乐
- 3 分手前夜别人强行占有了爱人
- 4 永远占有
- 5 不平等的爱情
- 6 锦衣不夜行
- 7 不是青梅竹马也要好好相爱
- 8 不爱无罪
- 9 冬天的栀子不开花
- 10 晾晒爱情
-

希腊神话30篇完整版
1、尼俄柏希腊神话2、乞丐奥德修斯来到大厅希腊神话3、俄狄甫斯和波吕 ..点击量: 3475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热门15篇
1、彭忒西勒亚希腊神话2、天马与王子希腊神话3、赫拉克勒斯为翁法勒服 ..点击量: 1997 | 时间: 2025-06-02 -

希腊神话600字锦集
1、美狄亚和埃厄忒斯希腊神话2、赫拉克勒斯和阿德墨托斯希腊神话3、围 ..点击量: 1372 | 时间: 2025-06-02 -

爱情故事100个
1、静候一次回眸爱情故事2、就是这个温度爱情故事3、单车上的爱情爱情 ..点击量: 2381 | 时间: 2025-06-02 -

中国历史故事全文九个
1、中国历史故事:盘点中国历史上那些经典阅兵中国历史故事2、军法始于 ..点击量: 1943 | 时间: 2025-06-02 -

格林童话十个内容
1、金钥匙格林童话2、金鸟格林童话3、蓝灯格林童话4、狼和七只小山羊格 ..点击量: 3220 | 时间: 2025-06-02 -

安徒生童话短篇五个
1、天鹅的窠安徒生童话2、梦神安徒生童话3、飞箱安徒生童话4、大门钥匙 ..点击量: 2509 | 时间: 2025-06-02 -

益智故事完整版1300字
1、顺势趴下并不是屈服的智慧益智故事2、龟兔赛跑益智故事3、认同自己 ..点击量: 1523 | 时间: 2025-06-02 -

罗马神话五个免费
1、狄安娜和阿克泰翁罗马神话2、俄狄浦斯的故事罗马神话3、庇格玛利翁 ..点击量: 1358 | 时间: 2025-06-02 -

历代名女名妓七篇推荐
1、谢道韫临事不乱历代名女名妓2、中国历史上十大名妓之死——玉堂春尽 ..点击量: 1640 | 时间: 2025-06-01
本站名称: 狸猫故事(m.limaogushi.com)
内容收集于网络或由网友投稿提供。
如有侵权请迅速联系本站,本站在核实后立刻作出处理!
Copyright ©狸猫故事 2019-2022 故事大全